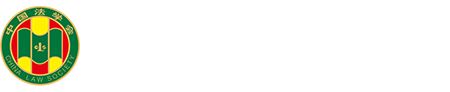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低空经济中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主要包括监测、通信和成像等通用航空领域。典型的监测任务包括边境和海上巡逻、搜救、渔业保护、森林火灾探测、自然灾害监测、污染测量、道路交通监视、电力和管道检查以及地球观测。一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在空中持续飞行数周甚至数月,也适合作为通信中继。还有一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已经被用于商业成像目的,如航空摄影和航拍视频。
随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技术和性能的发展,其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国内多个城市已开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物流配送试点,以深圳为例,2024年已实现无人机载货飞行77.6万架次,并开始规划跨境飞行、城际飞行、联程接驳、市内通勤等空中载人业务。随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同样的功能,逐渐进入公共航空运输领域,在民用航空法的修订过程中,需要首先明确以下两个重要问题: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否适用现行民用航空法律制度?现行公共航空运输法律制度能否调整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适用民用航空法律制度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否适用民用航空法律制度,取决于此类航空器能否被涵盖在民用航空器的范畴内。对此问题,可以从国内法和国际法维度进行回应。
从国内法维度,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属于民用航空法调整的范畴。民用航空法第5条从功能的角度,将用于执行军事、海关、警察飞行任务外的航空器均认定为民用航空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2条将无人驾驶航空器定义为没有机载驾驶员、自备动力系统的航空器。由此,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可以被认定为民用航空法意义上的民用航空器。
虽然民用航空法第214条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排除在民用航空法调整范围之外。但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58条规定,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以及有关活动,本条例没有规定的,可以援用民用航空法。笔者认为,这种互相援用的实际效果应是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适用独立的规则,但其民事用途则应回归民用航空法本身。
实践中,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针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称谓交替使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无人机这两个术语,但都将自身的调整范围限制在民事领域,并主要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管理问题。比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规定,“民用无人机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并从事非军事、警察和海关飞行任务的航空器。”《深圳市民用微轻型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民用无人机,是指没有机载驾驶员操纵、自备飞行控制系统,除用于执行军事、警务、海关执法飞行任务外的航空器”。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目前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规范体系,应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民用航空器,针对其管理方面制定专门规定。而对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其他方面,则应回归民用航空法的规定。
从国际法层面,调整民用航空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通过国际条约规定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纳入到现行国际民用航空法体系。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2《空中规则》,遥控驾驶航空器是指一架由遥控站操纵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可以认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调整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约等同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用语中的遥控驾驶航空器。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法律委员会第36届会议期间,其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局提交《与遥控驾驶航空器相关的法律问题(责任)》,提出《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有关航空器的条款同样适用于从事国际空中航行的遥控驾驶航空器。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法律专家看来,《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应适用于遥控驾驶航空器,需要根据遥控驾驶航空器本身的特殊性,适当调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部分条款的适用方式,并制定专门针对遥控驾驶航空器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综上所述,不管是国内法层面还是国际法层面,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都应被涵盖在民用航空器中,进而由民用航空法律制度调整。针对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民事用途时存在的特殊问题,可以调整现行规范或单独立法。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适用公共航空运输法律制度
从事货物运输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适用公共航空运输法律制度存在部分争议,但调整从事旅客运输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并无问题。原因在于有人驾驶航空器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进行旅客运输时,都使得旅客与承运人之间产生相应法律关系。当旅客出现人身伤亡时,由公共航空运输法律制度统一调整有人驾驶航空器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履行的旅客运输并无法律适用方面的歧义。
在履行货物运输时,有人驾驶航空器使得作为商事主体的承运人、托运人和收货人三方之间产生法律关系;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使得作为最终用户的消费者与终端服务商或商品提供商双方之间产生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同,使得航空货运法律制度适用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履行的货物运输至少有以下三方面需要调整:
第一,应取消出具航空货运单的要求。根据民用航空法第114条规定,应由托运人填写三份航空货运单,分别交承运人、收货人和托运人。然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履行货物运输时仅涉及两方主体,前述要求显然并不适配。出具航空货运单,主要是为了行使处置权和交付货物。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履行货物运输时,其本身就是向最终用户交付货物,前述交付航空货运单的功能在此种情况下无实质意义。
2025年2月,《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删除了现行民用航空法第116条,承运人同意未经填具航空货运单而载运货物的,无权运用责任限额的规定。《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第118条增加了货物运输应出具航空货运单的要求,但也明确航空货运单未出具或不符合要求或遗失的都不影响运输合同的存在或有效。考虑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货物运输时,航空货运单功能不明显,基于《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的规定,笔者建议不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载货时出具航空货运单做硬性要求。由航空运输合同调整消费者与终端服务商或商品提供商之间的法律关系,将极大便利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货物运输。
第二,应加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指挥控制链路被非法干扰,承运人免责的事由。民用航空法第125条第4款规定了货物运输承运人的免责事由,即“货物本身的自然属性、质量或者缺陷;承运人或者其受雇人、代理人以外的人包装货物的,货物包装不良;战争或者武装冲突;政府有关部门实施的与货物入境、出境或者过境有关的行为”。《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并未变更前述规定的实质内容。前述免责事由是以有人驾驶航空器为出发点,并不完全适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的货物运输,特别是第三项和第四项免责事由。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运行中,需要操控人员通过指挥控制链路遥控驾驶,如果被其他人非法干扰指挥控制链路,进而影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应明确承运人免责。
第三,应针对迟延本身规定承运人承担责任。民用航空法第126条仅规定承运人承担货物在航空运输中因延误造成的损失,《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未对该条作实质性修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载运货物的重要优势在于快速送达终端客户。因此,仅赔偿迟延导致的损失,降低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载运货物运输的吸引力。特别是承运人对于运送时间有专门承诺的情况下,应考虑将迟延本身作为损害赔偿的事由。
随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公共航空运输能力的不断提升,民用航空法律制度与之不适配的问题,必然影响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有序发展。2020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处成立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组。随着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越来越多地承担与有人驾驶航空器同样的功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也意识到现行航空法律制度必然面临调整,需要尽早着手研究。在民用航空法律制度能够调整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前提下,可行的方案是在民用航空法的修改过程中,制定专门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货物运输的条款。在国际层面,应推动制定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国际航空货物运输规则,能够针对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从事货物运输的特殊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规则。
〔作者张丝路 系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涉外法治视域中国际货物运输争议解决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3JY07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