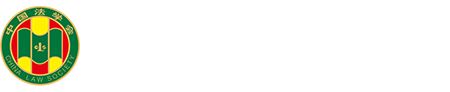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监察体制与检察制度的协同发展,是维护司法公正、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作为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协作配合的重要制度设计,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不仅是完善证据链条、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关键手段,更是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的实践成效
自行补充侦查是宪法规定的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在诉讼制度上的具体落实,其预设目标和制度价值主要是为了补强证据以弥补前期调查不足,通过对证据的检视实现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制约。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监察法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这一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职务犯罪案件的自行补充侦查权,同时强调了“必要时”这一前提条件,体现了权力行使的审慎性。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自行补充侦查的具体情形和操作规范,增强了其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自行补充侦查制度正日益凸显其重要价值。检察机关灵活运用这一权力,深挖案件线索、完善证据链条,有效提升了案件办理质效。
精准查明案件事实,提升案件质量。在职务犯罪案件中,自行补充侦查在精准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沈某某、郑某某贪污案(检例第187号)为例,在审查起诉阶段,因案件涉及复杂的期货交易专业知识和隐蔽的犯罪手段,检察机关建议监察机关调取涉案违法交易终端信息进行电子数据鉴定,同时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办案人员通过询问证人、调取微信聊天数据,交叉比对涉案期货账户登录数据和交易数据,排除账户被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并通过建立多个模型深入分析交易行为异常性,与专业人员研讨解决关键问题,最终成功指控犯罪。承办检察官细致审查资金流向,积极督促相关部门查封、冻结涉案财产,依法建议追缴赃款。此案例生动展现了自行补充侦查在全面查清犯罪事实、精准认定犯罪数额、深挖漏犯以及有效追赃挽损等方面的强大作用。
突破证据困境,补强证据链条。自行补充侦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补强证据以弥补前期调查不足。以河北石家庄的刘某受贿案为例,该案历经一审、重审后进入二审阶段时,主审法官认为案件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拟作出无罪判决。案件的难点在于:关键证人王某的《询问笔录》存在明显瑕疵,且王某已不幸去世,无法对笔录进行补正;受贿所用的银行卡未能起获,也无银行记录可证实资金往来;受贿款的去向不明。案件办理陷入僵局。面对这一困境,承办检察官果断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通过收集原办案人员出具的《情况说明》,并详细询问王某亲属,对存在瑕疵的询问笔录进行合法补正。在查找涉案银行卡时,检察官多次前往不同银行查询,凭借坚定的决心和专业的侦查能力成功锁定涉案银行卡。为查明受贿款去向,检察官系统梳理银行流水数据,结合其他关联证据,成功构建起完整的证据链。该案彰显了自行补充侦查在应对疑难复杂证据问题,尤其是在关键证人缺失等极端困境下的价值。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司法公正。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在江苏省新沂市新店镇原民政助理兼新店镇中心敬老院院长李某某贪污案中,针对李某某套取资金的去向问题,新沂市检察院与市监委共同研究后,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承办检察官到相关单位走访调查,补充调取书证,查清资金来源,补强了证明被告人贪污行为的证据。检察机关通过自行补充侦查,完善了证据链条,准确认定了犯罪事实,对监察机关的调查工作进行了有效监督。对于监察机关调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证据收集不规范、法律适用不准确等问题,检察机关应及时纠正,确保案件依法处理,实现司法公正。
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自行补充侦查能够避免案件被不必要退回补充调查,从而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在某大型企业系列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涉案人员众多、案情复杂,如果频繁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不仅会延长办案周期,还可能导致证据灭失或证人记忆模糊。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自行补充侦查的优势,针对案件中的证据问题迅速展开调查。例如,通过自行询问证人、调取书证等方式及时获取重要证据,使案件快速进入起诉和审判阶段。相比反复退回补充调查,合理运用自行补充侦查机制能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促进监检协作,完善工作衔接机制。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为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协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了工作衔接机制的不断完善。在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杨某贪污案中,杨某作为国有公司员工,负责管理安置房。针对其隐匿、出售安置房并获利的行为,龙泉驿区检察院与区监委、公安分局成立协调小组,经共同研究,检察机关遂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由检察长带队走访多个单位,明确安置房产权归属、核实杨某工作职责及房屋产权证办理流程,并询问购房者,最终查取关键书证和证人证言,为案件定性提供了关键证据。通过此类案件的办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逐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双方在自行补充侦查过程中明确了职责和权限,实现优势互补。例如,检察机关就专业性问题向监察机关咨询,监察机关协助检察机关调取相关证据,共同提升了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能力。
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的优化路径
健全法律制度,强化体系支撑。尽管相关法律对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作出了规定,但在实践中,法律规范仍存在模糊之处。例如,“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的“必要”标准缺乏明确界定,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时存在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应对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细化,明确“必要时”的具体情形和判断标准。可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必要时”的情形,例如增加“发现洗钱线索”等情形,为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启动自行补充侦查时提供明确的依据。
实践中不乏通过自行补充侦查认定洗钱犯罪的案例。如四川省检察院发布的“贪污贿赂类自洗钱”典型案例中的马某某受贿、洗钱案,广元市朝天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发现,马某某在受贿过程中多次使用他人银行账户收受贿赂款,再取现存入其姐夫易某某的账户用于支付购房款,其中马某某将4.99万元受贿款用于购买房屋的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后,可能涉嫌自洗钱犯罪。为及时固定完善证据、提高诉讼效率,朝天区人民检察院在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充分沟通并对案件定性及线索处置形成共识后,依法开展自行补充侦查。最终马某某对检察院指控其犯受贿罪、洗钱罪均无异议,自愿认罪认罚。
严格遵守原则,规范操作流程。关于自行补充侦查的程序规范,如侦查期限、证据收集方式等,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够具体详细,使得办案人员在实践中缺乏明确指引,容易出现操作不规范的情况。这不仅影响自行补充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还可能对案件质量产生潜在影响。为解决此类问题,需通过制定专门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对自行补充侦查的各个环节细化规范,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调研显示,某省就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出台了专门的工作实施细则,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应当严格遵守“退回补充调查优先,自行补充侦查例外”原则。具体而言,应遵循确有必要、严格依法、协同配合、稳妥谨慎等原则启动自行补充侦查程序。检察机关应充分尊重监察机关调查主体地位,避免职责混同,立足于查清案件事实,健全与监察机关协作配合机制,加强工作沟通,提前研判。对于基本证据体系已经形成、仅需查明个别具体事实或者补充个别具体证据材料的案件,可以展开自行补充侦查;对难以保证自行补充侦查效果的,慎重开展自行补充侦查。
除此之外,还应详细规定补侦期限、证据的收集和使用、具体的程序要求等。一是明确补侦期限。自行补充侦查本就属于审查起诉期限的一部分,无法单独设立期限。建议将补充侦查作为延长审查起诉期限的法定理由,比如若在审查起诉期限内不能补充侦查完毕的,可依法延长期限。二是细化程序要求。规范自行补充侦查中讯问、询问、取证、鉴定、勘验、检查、辨认等程序,严格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进行。三是完善证据使用规则。自行补充侦查所调取的证据在制作审查报告时应予以摘录,并在公诉案件审查报告中说明补侦相关情况;自行补充侦查结束后,应当将收集、调取的证据复印件移送监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形成的证据材料应单独立卷归档等。四是把握补侦要点。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被害人、证人时,重点核查相互之间的细微矛盾点及现有证据不够清楚、细致的情节,查明原因并作出合理解释。
强化监检协作,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自行补充侦查环节中仍存在案件信息传递上的滞后性。此外,对一些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标准不一致时,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
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建立健全长效沟通协调机制。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就职务犯罪自行补充侦查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二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案件信息实时共享和互联互通,提高信息沟通的效率和效果。三是明确双方在自行补充侦查中的职责和权限,规范协助程序,确保监察机关能够及时、全面地为检察机关提供协助。四是对于案件定性和法律适用方面的分歧,建立专门的协商机制,通过充分沟通和研讨,达成共识,确保案件依法处理。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的杨某贪污案为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提供了范例,促进双方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职务犯罪的合力,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作者邢晓芸,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务部副主任。
本文系国家检察官学院2023年一般项目“监检衔接机制研究”
(GJY2023NY06)的阶段性成果。〕
摘自《民主与法制》周刊2025年第2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