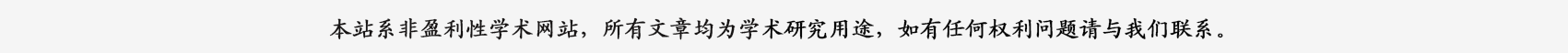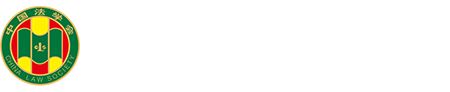当前,特大型城市及区域中心城市普遍面临地面交通拥堵和通勤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电动垂直起降器、无人机等为代表的飞行器,凭借其垂直起降能力、实时动态路径优化、按需响应服务、起降点部署灵活与不受地面道路资源限制等优势,展现出其在空中出租车服务、医疗急救转运、城市公共服务、高端商务出行等多个领域的应用潜力,为缓解交通压力、激活低空经济提供了创新方案。这种利用有人或无人驾驶飞行器在城市低空空域实施按需运输的交通模式即城市空中交通。作为行业引领者,广东亿航等企业已取得载人无人机运营许可,意味着城市空中交通已从技术蓝图开始向实际运营迈进。
然而,技术革新常伴随权利博弈:城市空中交通发展可能触及居民环境权、隐私权及空间权等权益。如何通过技术规制、利益补偿与公众参与等手段,以民生福祉为中心,兼顾技术创新,在保障公众出行便利与社区私权保护之间建立有效平衡,推动城市空中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是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中亟须研判的问题。
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的冲突
隐私、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风险。为保障飞行安全,城市空中交通飞行器的通信导航监视系统需采集地理及环境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居民住宅及其内部状况、个人活动轨迹及个体特征等敏感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收集后会被存储于专用数据库中,并在运营企业、空域管理部门等多个主体之间进行共享。这使居民的隐私信息、出行习惯以及居住数据面临泄露或被不当传播的风险。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数据处理需经个人同意,但城市空中交通广域数据采集的特性使得逐一获取授权极其困难。因此,城市空中交通领域可能潜藏着未经授权的信息采集、存储以及共享传输等侵犯个人隐私信息的非法行为。
噪声污染与生活安宁权冲突。作为城市空中交通飞行器的主力载体,电动垂直起降器的噪声污染或将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电动垂直起降器的运行噪声较直升机低,但其高频噪声与人耳听觉敏感区间重合,对社区居民的生活安宁构成显著影响。人若暴露于高频噪声环境,可导致耳鸣、听力衰退、诱发失眠、焦虑及注意力障碍,促使肾上腺素分泌异常,增加高血压及心血管疾病风险。若不解决好噪声问题,空中公共交通诉求与居民生活安宁诉求必将产生激烈对抗,拖累城市空中交通可持续发展步伐。
低空飞行权与居民安全权的冲突。经民航局依法授予运营许可,低空飞行运营人便获得低空飞行权利。但公众对城市空中交通飞行器安全的担忧,不止于传统飞行安全,还体现在新的安全方面:一是其高度依赖自动化系统,易受远程网络攻击或出现系统故障,威胁飞行安全;二是在城市环境紧急着陆,会增加地面人员和财产风险;三是电池系统碰撞易起火,引发火灾担忧;四是频繁飞行可能导致居民心理不适;五是电子设备产生的电磁干扰,会影响其他航空器和地面设施运行。
城市空中交通发展起步阶段,因缺乏飞行安全历史数据,公众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担忧更甚。事实上,公众缺乏对城市空中交通安全的信心,并非反对低空飞行。制定和执行更严格的法律标准,提升城市空中交通飞行器的安全技术水平,适度向公众披露信息,是提高公众信心的有效措施。
城市空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与社区空间权的冲突。飞行器起降点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空中交通的核心要素。然而,起降点的规划与建设对周边社区具有一定影响:社区居民因担忧安全、噪声、隐私泄露,或建筑物遭受震动、碰撞等,可能拒绝在其附近建起降点;还有可能因对楼顶或小区空地享有共有权及相应高度的空间权利,否认飞行器对该空间的使用权。此类基于空间利用产生的紧张关系,无疑会成为城市空中交通发展的又一阻碍。
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权益的相对性
城市空中交通与社区居民权益的冲突实质。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的冲突本质是低空交通发展与传统民事权利的矛盾。这种矛盾既包含新兴的城市空间立体利用方式对传统空间利用结构的冲击,也凸显了隐私权、环境权、空间权等传统民事权利在空间立体化发展中的适应困境。低空交通发展作为制度基础,其核心是运营人依法享有的经营权。一旦取得运营许可,低空飞行即成为经营者的合法权利,不应受不当干扰。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隐私权、安全权等作为基本权利,具有法定不可减损性。如此一来,经营人与社区居民在内容上存在冲突的上述权利在同一物理空间的并存便具有对抗性。
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冲突的相对性。城市空中交通的发展旨在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满足有时效性要求的服务,以提升民生福祉,促进社会进步。虽然在发展初期服务价格不菲,但随着技术成熟,城市空中交通服务价格将持续下行并最终降至大众可接受的水平。此外,城市空中交通可在应急救援、医疗救助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这种与社区居民利益的契合性为调和二者潜在的冲突提供了可能。
然而,由于不同阶段和不同主体对城市空中交通的需求和选择存在差异,居民在不需要该项服务时可能会表现出抗拒心理。加之城市空中交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技术依赖性,其对居民权益的影响会随着技术进步和阶段推移而衰减。因此,城市空中交通在发展初期与社区居民权益的冲突相对明显。
鉴于此,城市空中交通的治理应当基于其与社区居民权益的内在一致性,结合其冲突的相对性与阶段性规律,依循法治化治理路径,建立多方主体的权益平衡机制,实现低空经济发展与社区良好秩序的协调共生。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依法治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发展城市空中交通。如前所述,城市空中交通的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具有宏观的一致性与微观的差异性。在发展城市空中交通过程中,须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标,既要避免因局部矛盾否定整体价值,又要警惕以发展名义损害居民权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保障民生福祉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基准线。
在治理路径上,应构建以技术控制与社区协商为核心的治理方案:通过社区协商机制,搭建多方对话平台,吸纳和了解居民诉求;通过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优化飞行器起降频次、航线规划与时段管理,减少飞行活动对居民的影响;加大对安全与降噪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飞行器安全与噪声控制技术升级;开展权益影响评估,运用大数据模拟技术预判噪声扩散轨迹,确保飞行噪声控制符合居民区噪声标准。
以法治方式解决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中的权益冲突。在解决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冲突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当不同权利发生冲突时,应根据权利的位阶,即“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人格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原则与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原则处理。据此,人格权、健康权等自然人基本权利在位阶上高于企业经营权。因此,城市空中交通运营人的经营权的行使需符合比例原则与公共利益要求,不得突破居民基本权利保护底线。比如,居民的健康权、隐私权等权利具有不可克减性,城市空中交通运营人不得因提供经济补偿而减免法定降噪义务,在噪声超标情形下,运营人须履行技术降噪、航线优化等义务,不得通过协议规避降噪责任。同时,居民维权须恪守依法维权原则,以合法方式表达诉求。
准确界定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与社区居民权益的法定范畴,是判断城市空中交通项目是否影响社区权益的前提。因此,需依据民法典、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以下权利边界:其一,通过空域权属划分确定城市空中交通专属飞行空域与社区不动产附属空间的界限。其二,地面起降点选址应遵循相邻关系规则,私人财产权为公共利益让渡时需给予合理补偿。其三,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管理规定》,严格设定城市空中交通合法采集信息的范围。其四,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及民航局标准,明确噪声达标情况下社区居民的合理容忍义务。其五,基于安全生产法与民法典,确立城市空中交通运营人安全飞行义务的绝对性与居民人身财产安全权利的优先性。
确保经营许可与航线设置的合理性。城市空中交通的发展必然对社区居民权利形成一定限制,因此其经营许可与航线规划必须满足适当性、必要性、均衡性的正当性标准。就适当性而言,航线规划应有效提升城市交通效能,如起降点设置于交通网络薄弱的郊区,反而可能因配套不足导致效率损失。必要性要求严格遵循最小损害原则,应通过技术模拟与空间评估选择对居民生活影响最小的地点设置起降点与规划飞行路径。均衡性则强调公共利益增量必须实质大于居民权益损失,需通过成本收益分析量化评估交通效率提升与噪声污染、隐私风险等负面影响。凡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城市空中交通项目,依法不应给予经营许可。
尽快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法与《城市空中交通管理条例》。目前,我国缺乏专门规范低空经济与城市空中交通管理的法律法规,应当尽快制定低空经济促进法和《城市空中交通管理条例》,为低空经济的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一是在低空经济促进法中设立“社区权益保护”专章,通过权利义务规则统筹城市空中交通产业发展与居民权益保障,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原则与制度:第一,权益平衡原则。建立动态协调机制,通过技术优化、经济补偿、航线避让、时段限制等手段,最大限度降低飞行活动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第二,数据采集实行“最小必要”原则。禁止收集与飞行安全无关的个人信息,推行“非必要数据收集即删除”制度与技术标准,避免非飞行安全所需信息被查看、储存和共享传输等情况发生。在住宅区200米范围内禁止使用穿透性监测设备,并设立“低空数据禁采区”。运营企业需公示数据采集清单,明确存储与销毁时限,保障公众知情权。安全相关数据采集可豁免知情同意,但须建立严格的分级审批与使用监管机制。第三,划定空间权属范围,完善低空飞行基础设施选址规划制度。应当规定从建筑物顶部起算,真高50米以下垂直空间为社区物权人共有空间,未经许可禁止飞行器穿越,以填补民法典未明确空间权高度的漏洞。起降点选址须避让居民区、学校及医院等敏感区域,强制实施电磁辐射、环境影响与安全性评估,确保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布局对社区影响最小化。第四,健全社区协商制度。建立社区低空事务协商委员会,参与项目监督与纠纷调解。将城市空中交通航线规划、起降点建设等重大事项纳入社区听证程序,听证结果作为项目审批前置条件。第五,确保技术合法化。明确城市空中交通运营人提升飞行器降噪与安全性能的法定义务。在适航标准中强制纳入降噪技术与安全设计标准,强制企业淘汰不达标机型。建立社区影响指数实时监测制度,对噪声、隐私暴露度、房价波动情况及居民安全情况等核心指标进行监测分析,如果达到严重程度,应当暂停城市空中交通的商业飞行,仅保留急救等公共服务飞行。第六,完善补偿救济机制。建立对受损者补偿机制,对财产贬损与生活安宁受影响的居民实施合理补偿。实行举证责任倒置,降低居民维权成本。同步明确妨碍飞行的法律责任,公布合法维权渠道,通过疏堵结合实现低空经济与社区权益的协同发展。
二是制定《城市空中交通管理条例》,进一步细化低空经济促进法的制度要求:第一,明确城市空中交通航线划设与管理制度。航线需统筹国土与空域规划,遵循安全、环保及高效利用资源原则,避开生态敏感区、文物保护单位及人口密集区,确保电磁环境达标并与地面交通系统衔接。影响社区权益的航线应优化调整,禁止在住宅区、学校、医院周边500米内设置起降点,夜间22时至次日6时禁止在居住区上空飞行。第二,规定强制技术规则。禁止噪声不达标飞行器运行,强制配备主动降噪、电子围栏及自动避障系统。第三,明晰社区权益保护规则。除紧急救助外,禁止飞行器进入居民建筑专属空间。严禁采集与安全无关的个人生活轨迹、生物特征及设备信息,明确“非必要信息收集即删除”实施办法和标准,确保非必要、与安全无关的信息在收集当时即自动删除。预先披露的信息收集清单应当在航线范围内的社区进行提前公示、接受质询,并提供拒绝采集的程序和渠道。明确飞行器载客装卸时不得启动悬停,确保安全作业。
三是在低空经济促进法制定之前,于正在修改的民用航空法中设立“低空经济”专章,规定前述制度,作为过渡方案,以解决目前的法律缺位问题。
作为低空经济关键应用场景,城市空中交通发展伴随着公私权益的博弈。应以低空经济促进法为核心,统筹各方权益,兼顾保障民生安宁与释放低空经济潜力,实现立体交通创新与民生福祉的协同发展。
〔作者王立志,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本科研项目“空域改革视域下的低空经济促进法律制度研究”(NJ202404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