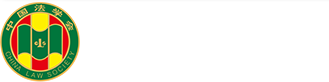文/耿红丽
医保基金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百姓的“救命钱”,其合理、高效、安全的运行关乎每一个参保人的切身利益。但近年来,一些不法医疗机构通过虚构诊疗、伪造处方等手段骗取医保基金的案件频发,暴露出监管漏洞、制度缺陷及医疗行业诚信危机。本文结合多起同类案件,分析骗保行为的操作模式、社会危害、成因及治理路径,旨在为完善医保监管体系提供参考。
一、不法医疗机构骗保手法及特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健康需求日益增长,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国家投入大量财力保障庞大的医疗机构运转。一些不法医疗机构不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吸引患者、获取收益,而是窥觊国家医保基金,制造虚假医疗,以虚假处方与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相关人员通过伪造、变造处方等医疗文书,虚构医药服务项目或夸大医疗费用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笔者结合实践案例概括为以下几种主要手法。
(一)“阴阳处方”或“鸳鸯处方”。 开具两套处方,一套虚高药品或诊疗项目,用于医保报销,一套用低价替代药品或简化诊疗用于实际治疗。如2013年至2024年,四川广元某医院采用开具高价药的电子处方向医保部门骗取医保资金,同时手写处方开出功能类似的廉价药给病人使用,骗取医疗保险基金749万余元。
(二)伪造或篡改处方。虚构患者信息、诊疗记录或药品用量,伪造检查报告、病历等医学文书作为处方依据。一般是药店与医药代表勾结,使用虚假处方销售高价药品并骗取医保报销。比如,2020年,西安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伪造处方、无处方违规销售等问题,涉及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25万余元。
(三) 虚增药品或诊疗项目。在处方中虚增患者未使用的药品数量或未实施的检查治疗项目,如虚构手术、多计护理天数、“大处方”等。2022年郑州某民营医院,以免费住院、住院有好处费等理由拉拢患者违规住院,开具含全蝎、蜈蚣、水蛭等高价中药的处方,实际未提供药物,半年多时间,骗取医疗保险基金120万余元。
(四)虚构病情诱导治疗。通过夸大或捏造病情,诱导患者接受不必要的高价手术或用药。2022年至2025年,天津河东某眼科医院,虚构诊疗事实、虚假手术等方式,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上亿元。
二、社会危害
虚开处方是医疗领域常见的违法违规行为,其危害具有多维性和连锁效应,不仅涉及医保基金安全,还威胁患者健康、破坏医疗秩序,并引发纠纷与社会信任危机。
(一)造成医保基金流失。2023年全国推动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制度,为群众就医用药提供了极大便利。随着“医药分开”的改革推进,越来越多的处方从医院流向药店。全国零售药店处方药市场规模持续扩大,截至2024年5月,全国零售药店处方药市场规模为1013亿元,同比上升1.3%,与之相随的是虚假处方、先药后方、未经执业药师审核销售处方药等行业积弊。2024年哈尔滨4家药店通过伪造手写处方,不同医生印章,对应不同的科室和用药,用假处方购买临床价值高、患者急需、替代性不高的“特药”,涉及金额超亿元,导致医保基金流失6223万元。
(二)危害患者健康。虚假治疗延误病情,过度医疗加重经济负担。湖南恶魔医生刘翔峰在湘雅某医院工作期间,为牟取额外手术费用,单独或伙同他人夸大患者病情、虚构患者病征,给6名不具备相关手术指征的患者实施手术,致5人重伤、九级伤残,1人轻伤。
(三)损害社会对医疗机构的信任。个别不法医院以“包吃包住”“出院送药送钱”“免费接送”“不花钱”为噱头吸引城乡居民住院。老年人和低收入群体医疗需求高,医保报销依赖性强,对政策了解不足,易被“免费医疗”噱头吸引,主动或被动参与骗保链条。群众及参与者往往因此对中小医院,特别是民营医院产生强烈的不信任感,生病就往大医院挤,造成医疗的过度集中。同时,当医保账户因骗保行为而不足或受限时,会对医疗机构产生强烈的仇恨感,导致伤医等恶性案件的发生。
三、成因的多维度解析
医保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具有历史性、广泛性、顽固性等特点。当前医保基金监管仍处在“去存量、控增量”的攻坚阶段,在严打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人心存侥幸、顶风作案,不收敛、不收手,究其原因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一)利益驱动与行业生态。特别是一些民营医院经营困难,盈利压力大,为持续经营或追求利益最大化,走上欺诈骗保的“捷径”。2019年1月—2023年8月,国家医保局官网公布的179件欺诈骗保案例中,民营医院占比高达29.1%,累计欺诈骗保金额8461.12万元。存在灰色利益链,医生、药商、医保经办人员在虚假用药、虚构病历、虚设检验、虚记耗材等环节分工明确,甚至设立专人负责“应对医保检查”,组织化、分工化程度越来越高,团伙化、专业化特征愈发明显,形成分赃网络。
(二)监管体系缺陷。一方面监管力度不够。横向上,卫生健康部门作为医疗机构服务管理的主导部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人数少且缺乏专业性人才,监管力量薄弱,同时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小,与其他政府部门平级,开展工作时协调能力有限,统筹组织性不足。纵向上,多层级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多重部门重复监督执法,出现监管空白和重复监管并存现象。另一方面,监管手段信息化程度不高。个别民营医院骗保从“体检式”“休假式”“挂床式”转为“真假掺杂式”,传统监管手段很难发现。医保报销依赖纸质或电子单据,易被伪造。政府数据“部门化”现象明显,医疗机构与医保部门数据未实时互通,难以及时发现异常,系统建设无法满足实际监管需求,尤其在处理异地报销结算业务时局限性更加突出。事后监管为主,依赖举报和抽查,缺乏事前风险预警机制。
(三)法律与政策滞后。一是联合执法程序不完善、行刑衔接机制不通畅。一些涉嫌骗保刑事案件被迫降级为行政处罚,处罚威慑力大打折扣,欺诈成本降低,部分案件仅处以罚款,缺乏刑事追责震慑力。上述179份案例中,虽然违约案件的欺诈骗保累积金额远高于违法案例,且涉嫌骗保的平均金额是违法案例的3.4倍,但是定性为违法与违约的分别占43.6%和26.3%,其中最终被判定为犯罪的案例仅45例,占25.1%。二是法律法规适用争议较多。2023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药机构80.2万家,处理违法违规机构45.1万家,违法违规机构占比56.23%,可见医疗机构违法违规的数量之大。目前,我国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有社会保险法、保险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但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基本医疗保险或医疗保障的法律。目前诈骗罪与医保违规行为的界限模糊,部分案件量刑标准不统一。伪造病历文书等报销凭证、虚构药品和耗材等医药服务项目、诱导住院、冒名住院、虚开费用单据等虚假医疗等只定性为严重违规行为。2024年2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对严重违规行为有相关规定,但对如何认定过度诊疗缺乏客观标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
四、治理对策与建议
各级医疗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加医疗资源有效供给、加速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主力军,对于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需求,推动医疗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医疗机构骗保案暴露了医保监管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需通过技术赋能、法律严惩、制度优化与社会共治形成合力,构建“不敢骗、不能骗、不想骗”的治理生态。
(一)强化技术监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制定政务数据和数据开发利用相关规范制度,构建统一的医疗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健全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一是消除数据壁垒。建立跨部门跨系统的标准化信息共享和多元协同机制,联通医保、人社、民政、卫健、财政、税务、银行等各类部门和单位,实现各级政府部门纵向联通,解决“数据孤岛”现象。二是加快推动大数据监管试点成果推广应用。不断完善医保基金欺诈骗保行为的大模型,构建医保骗保行为智能信息预警系统,探索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医保数据管理,实现医疗记录和费用结算的不可篡改和实时共享,减少虚假报销风险。三是加强对药品的监管。借鉴欧盟做法,每种药品在生产时会被赋予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虽然流通过程中不强制要求次次扫码记录信息,但在患者购买药品后,系统会记录该药品已售出,不能再进入流通使用环节。全面推进药品追溯码监管应用,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等行为。
(二)完善法律制度。一是完善政策法规。明确分解住院、重复检查、过度诊疗等法律概念和内涵,制定出台关于过度诊疗等标准,清晰界定如何判断过度检查,明确收售“回流药”的法律责任。建立案例库,将实务中的典型案例编入其中,以案说法,不断统一执法尺度。建立专业的仲裁机构以及设立人民陪审员制度。二是建立行业黑名单。完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加大对违法者、涉事医院的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对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除了追究刑事责任,还应该明确终身禁业,并对涉事医疗机构进行更严厉的处罚。
(三)完善多环节监管体系。一是加大源头监管。提高病历抽检随机性,严查病历描述模糊化、模板化、不合理医治等问题,提高药品出售及报销流程透明度,审查药品出单记录真实性与完整性,提高药品出单记录与处方审查频率,增加药房药品库存与清单的核实频率。二是严厉打击医保骗保销赃下游路径。对药品机构进行抽检,确保药品来源正规和合规。三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监管。委托配备医保、医疗、数据监测及法学领域专业人士的第三方机构对高风险医院进行不定期突击检查。
(四)提升行业自律与公众意识。一是压实定点医药机构自查自纠责任。全面落实定点医药机构相关人员医保支付资格管理制度,实行“驾照式记分”管理。二是提升医师职业道德。加强典型案例宣传教育,将反骗保教育纳入医师执业考核。三是鼓励社会监督。积极落实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关于举报欺诈骗保进行奖励的制度,并视欺诈骗保数额提高奖励上限。加大对患者及医护人员举报违规行为的奖励和保护力度,简化兑付流程,提升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