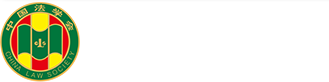民法典第1232条对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条件及法律后果作出了规定,突破了我国长期以来在环境侵权领域固守的填平原则。但在实践运用中,“被侵权人”的合理界定、“故意”“严重后果”“相应”的判断等皆需在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才能有效发挥示范性惩罚的制度功能,既实现其制裁与警示的惩治作用,又避免出现赔偿金过高或畸低的不当做法。
关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权利主体的范围是否包含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社会组织,笔者持肯定态度。其一,环境侵权诉讼可按照提起主体的不同分为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民法典第1232条在适用条件中并未明确此规定仅适用于私益诉讼,所以其理所当然包括现行法律体系下的两大类型,且民事诉讼法第55条明确了法律规定的机关及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合法地位。所以“被侵权人”除了直接受害人之外,还包括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其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惩罚性赔偿具有“同质性”。惩罚性赔偿通过惩罚、教育等一系列功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最大化保护,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弥补、涵盖私益诉讼中未得到保障的部分受损利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目的及功能更多的偏向于公法,而其实施程序却又在私法的框架内,是通过私法机制来实现本应由公法来承担的特殊使命的制度安排。透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关系各要素,无论是启动主体的公权力属性,还是作为客体指向的公共利益,其实质上皆立足于公共事务,已经对传统民事诉讼有所突破,兼备了一定的公法属性。据此,两者在运用机理上的同质性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运用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其三,“公共利益”的特殊属性要求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深度参与。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社会组织提起的生态环境民事公益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大多都是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涉及人数多的深层治理难题,如果允许对破坏生态较轻的行为可主张惩罚性赔偿,而对其更重的行为却只能采取“同质补偿”,显然不利于民法典“绿色原则”的贯彻实施,也阻碍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功用的发挥。
我国民法典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采取无过错侵权的归责原则,即无论行为人有无过错,都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但作为例外,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却需证明侵权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过错,即其具有故意的主观心理状态。因此便排斥了因加害人过失所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形。而对于故意的判定,实践中往往采取“明知+欲求”的要素分解法,在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必然或者可能发生危害后果后,进而通过“行为外观”判断其是否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在实践中主要包括如下情形:(1)在受到行政处罚后继续实施原违法行为的;(2)实施行为的手段具有隐蔽性,譬如:偷排、逃避检查、关闭录像等;(3)依据一般社会观念能够感知其行为具有违法性或者违背同行业领域所共知的专业性认识;等等。
作为结果要件的“损害后果”无非包含人身、财产、环境权益三种样态,其重点在于如何规范阐释损害程度的严重性,并非指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都可主张惩罚性赔偿,而只有当损害后果达到“严重”的程度时,才有该制度的适用余地。但是如何界分一般损害后果与严重损害后果,相关法规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可具体参考如下因素:(1)污染区域具有特殊性,譬如水源地、生态保护红线内;(2)污染面积、污染物数量超过一定限度或者污染物类型具有放射性等特殊属性;(3)造成的财产损失超出一定数额;(4)受害人数众多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等等,具体可参照适用《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目前立法层面主要存在四种模式,一是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10倍或3倍的固定倍数计算方式;二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赔偿2倍以下的最高限模式;三是商标法同时规定1倍以上5倍以下的上下限模式;四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关于“相应”标准的计算模式。在环境侵权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与威慑功能要求在确立“相应”标准时既不能过低,对违法行为人再次实施该行为或者同行业其他从业者“效仿”立起规矩,在“所得”与“所失”之间形成较大反差,经行为人权衡无实施该违法行为理由及勇气。也不能超出违法行为人的实际承担范畴,使其因为诉讼陷入经济危机。故此,现阶段立法上对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的“相应”标准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及社会特殊阶段的基本要求,其意旨就在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与妥适。但在司法办案过程中,如何在准确把握惩罚性赔偿功能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更重的经济负担实现遏制违法行为人、教育他人之目的,需综合考量违法后果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人的主观悔过状态、经济能力、获利情况及前期采取措施修复受损环境的现实表现等因素,通过对环境造成的损失这一特定基数,乘以不同的倍数得出惩罚性赔偿的最终数额。而关于“乘数倍率”的计算,应当由办案人员结合上述裁量因素,在1倍以上10倍以下的区间内合理确定。此外,大气污染法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分别确定了10万元与50万元的最高额惩罚限制,从目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偏低,虽然一定程度上可实现救济功能,但其预防、警示功能却并未得以彰显。因此,对于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范围的设置,应当采取“比例倍数”模式。
(作者分别为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兰州铁路运输分院检察长、检察官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