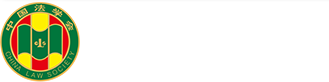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正当防卫”一词,虽始见于近代刑法,但其法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素有渊源。
“第二十条”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因
□中国古代法律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制度,但历朝历代都存在与之类似的规定,形成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防卫减免制度”,其中的部分规范值得反思和借鉴。
□中华法系以稳定的价值体系为依托,孕生于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独有文化,其防卫制度更有传统中国独特的法制内涵,对当今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一是注重维护“家庭”权益,二是对护卫直系尊亲属作出特殊规制。
近期热映的电影《第二十条》,唤起了人们对刑法第20条规定的“正当防卫”的高度关注。“正当防卫”一词,虽始见于近代刑法,但其法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素有渊源。这一曾被称为“沉睡条款”的规定,是否能从中国古代法律寻求历史镜鉴?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古代没有“正当防卫”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正当防卫沿于复仇”。“复仇”与“防卫”二者概念相差甚远,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古代法律尽管没有明确规定正当防卫制度,但历朝历代都存在与之类似的规定,形成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防卫减免制度”,其中的部分规范值得反思和借鉴。
正当防卫制度的早期萌芽
中国古文献与正当防卫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秋官司寇·朝士》:“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郑司农云:“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贾公彦《周礼义疏》释曰:“盗贼并言者,盗谓盗取人物,贼谓杀人曰贼。乡据乡党之中,邑据郭邑之内。家人者,先郑举汉《贼律》云。牵引人欲犯法,则言家人者欲为奸淫之事,故攻之。”根据郑司农的注释,汉代已有“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等不法行为,当时“格杀之无罪”的规定。所谓“格杀”,即击杀,相拒而杀曰格杀。但汉代的规定比较粗泛,对“无故入人宅”的时间,没有规定;对“格杀”的施行者也没有说明。
魏晋南朝未见相关法律,但南齐袁彖为庐陵王谘议时曾发生苟蒋之兄弟杀沙门(即僧人)案:时南郡江陵县人苟蒋之弟胡之妇为曾口寺沙门所淫,夜入苟家,蒋之杀沙门,为官司所检,蒋之列家门秽行,欲告则耻,欲忍则不可,实己所杀,胡之列又如此,兄弟争死。江陵令宗躬启州,荆州刺史庐江王求博议。(袁)彖曰:“夫迅寒急节,乃见松筠之操;危机迥构,方识贞孤之风。窃以蒋之、胡之杀人,原心非暴,辩谳之日,友于让生,事怜左右,义哀行路。昔文举引谤,获漏疏网;蒋之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实伤为善。”由是蒋之兄弟免死。
此案明显为沙门夜入蒋家,与苟胡之之妻通奸,其兄蒋之当场杀死沙门。依当时法律,本该处死凶手。但兄弟二人都说人是自己杀的,江陵县令启奏荆州刺史。刺史征求下属意见,袁彖的奏议只是从“原心非暴”,“友于让生”的义举角度,并引用“文举引谤”的典故。是说东汉末年,名士张俭得罪宦官,受到通缉,投奔孔融(字文举)之兄孔褒,后事泄露追责,孔融主动承担责任。由此证明“蒋之心迹,同符古人”。这有点“经义决狱”的味道。只有“原心定罪”的思想,尚没有形成“正当防卫”的原则。
正当防卫原则的确立和发展
唐代修律,设“夜无故入人家”条:“诸夜无故入人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疏议曰:“夜无故入人家”,依刻漏法:昼漏尽为夜,夜漏尽为昼。谓夜无事故,辄入人家,笞四十。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登于入时,被主人格杀之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谓知其迷误,或因醉乱,及老、小、疾患,并及妇人,不能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若杀他人奴婢,合徒三年,得减二等,徒二年之类。问曰:外人来奸,主人旧已知委,夜入而杀,亦得勿论以否?答曰:律开听杀之文,本防侵犯之辈。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辨,纵令知犯,亦为罪人。若其杀即加罪,便恐长其侵暴,登时许杀,理用无疑。况文称“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即明知是侵犯而杀,自然依律勿论。《唐律》曰:“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疏议曰:“已就拘执”,谓夜入人家,已被擒获,拘留执缚,无能相拒,本罪虽重,不合杀伤。主人若有杀伤,各依斗法科罪,至死者加役流。《唐律》的这条规定,确定了“夜无故入人家之罪”,只要有犯此罪者,无论是否有其他罪行,都要笞四十。若主人当时当场杀死侵入者,无罪。也就是主人有实施正当防卫的权利。
《唐律》此条与《汉律》比较,一是明确必须是“夜无故入人家”,而汉律没有提时间早晚,唐代有“夜禁”之法,“诸犯夜者,笞二十”,平人夜间无故不得出门上街,但犯即罚。二是唐只提“入人家”,“家者,谓当家宅院之内”,汉则包括“室宅、庐舍、车船”等居所。三是《唐律》但言“无故”,没有其他条件,汉代还有“盗物”“贼杀”及“奸淫”等情,故民间有谚语曰:“夜入人家,非奸即盗。”四是唐规定只有“主人”才能实施防卫权,汉则没有提谁“格杀无罪”。五是唐强调“登时许杀”,汉言“其时”,似乎不如唐严谨。汉唐都有“无故”的明文,即没有正当理由。但汉对《周礼》中“盗贼军乡邑”释为“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似乎阵势洪大,说的是群盗、群贼。至于汉之“牵引人”,应该是强略人口,贾公彦据《唐律》释为“奸淫之事”。前引南朝之例,杀入室犯奸的沙门,也要判死刑。而唐代对于入室行奸者,主人即使事先知情,杀之亦无罪。疏议曰:“律开听杀之文,本防侵犯之辈。设令旧知奸秽,终是法所不容,但夜入人家,理或难辨,纵令知犯,亦为罪人。若其杀即加罪,便恐长其侵暴,登时许杀,理用无疑。”《唐律》明确规定,实施防卫的权利不是无限的,若明知入室者并非或不能侵害自己及家人,而将其杀伤者,依斗杀伤律,减二等处罚。若已将侵入者捕获,又将其杀伤者,以斗杀伤论罪,至死罪者,处加役流。可见,唐代的防卫制度涵盖了排除“事后防卫”正当性的理念,同时强调要有“不法侵害”。
此外,《唐律》还有关于直系亲属受到攻击时的防卫规定,“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谓子孙元非随从者。”疏议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理合救之。当即殴击,虽有损伤,非折伤者,无罪。“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谓折一齿合杖八十之类。“至死者”,谓殴前人致死,合绞;以刃杀者,合斩。故云“依常律”。注云“谓子孙元非随从者”,若元随从,即依凡斗首从论。律文但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不论亲疏尊卑。其有祖父母、父母之尊长,殴击祖父母、父母,依律殴之无罪者,止可解救,不得殴之,辄即殴者,自依斗殴常法。若夫之祖父母、父母,共妻之祖父母、父母相殴,子孙之妇亦不合即殴夫之祖父母、父母,如当殴者,即依常律。
此有唐穆宗时之案例可为证:(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京兆府云阳县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征之,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莅角抵力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权之,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臣职当谳刑,合分善恶。”敕:“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孙革的奏谳,引经据典,务在开脱康买得的死罪,从“圣化”“孝道”,到“原心定罪”,句句在理。穆宗仅批“减死罪一等”,即流三千里。这也是对礼与律之间所做的调整。可知,唐代对防卫权的限制还是很严的。
明清以后,这方面有所改动,《大明律》的“父祖被殴条”前文与《唐律》同,后又增加了一句:“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大清律例》律文与此相同,但增加条例:“人命案内,如有父母被人殴打,实系事在危急,伊子救护情切,因而殴死人者,于疏内声明,援例两请,候旨定夺。”这样看,确实比明律更严谨了。
“正当防卫”一词,始用于近代刑法是在清末的《大清新刑律》和北洋政府的《暂行新刑律》,其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同时,《大清新刑律》附录的《暂行章程》规定:“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也规定:“正当防卫”,“于尊亲属不适用之”,“但嫡母、继母及夫之尊亲属出于虐待之行为者除外”。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刑法》规定:“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罚;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刑法第20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中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中国古代正当防卫制度的当代价值
中华法系以稳定的价值体系为依托,孕生于中华民族血脉传承的独有文化,其防卫制度更有传统中国独特的法制内涵,对当今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一是注重维护“家庭”权益。汉代对“无故入人室宅”者“杀之无罪”,唐律设“夜无故入人家之罪”,且“登时杀之勿论”,以“家宅不可侵犯”的法律理念彰显“家”的重要地位,这种对家庭的重视和对“家”的特殊情感已铭刻民族文化精髓。“朱凤山案”中,家主朱凤山因他人跳入其院墙实施侵害而捅刺侵入者,二审之所以改变一审定性和刑罚,认定其属于防卫过当,从有期徒刑十五年改判有期徒刑七年,也是对一般民众爱家护家朴素情感的肯定,同时有必要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这一传统法律观念,充分考量维护家庭利益行为的正当性。
二是对护卫直系尊亲属作出特殊规制。公众价值判断的背后存在深厚的民族集体意识和集体认知,伴随社会变革和法制演进,“亲亲尊尊”伦理性规定虽不复存在,但对父母的尊崇仍作为思维习惯或共识性价值留存于公众心中。当父母遭受类似“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不法侵害时,子女应如何作为?最终司法机关认可了子女激愤情绪的合理性,以及在此情绪支配下采取护卫近亲属的正当性,这种观念早已在唐律中建立,并在明清律法中强化,也有必要成为今后涉尊亲伦理案件办理的重要参考。
(作者分别为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