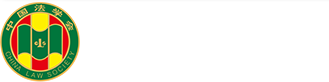内容提要:《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首次将法定代表人越权缔约行为区分为超越法定权限和超越意定权限,并分别赋予其不同法律效力。对超越法定权限缔约行为的评价受制于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的两个刚性约束,即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以及代表机关法定。在法网严密的现代管制社会中,评价超越法定权限缔约行为涉及两种难以调和的价值:推定知法的法治原则与信赖保护。代表权法定限制的实质是就特定事项对法人意思形成的法定程序要求,体现的是法人意思形成的程序正义,其性质为自然法规范,故推定相对人应知和要求相对人尽合理审查义务并不苛刻。此时,相对人应循法审查法人章程。合同法应承认法人意思形成过程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认定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缔约行为为法定代表人而非法人的意思表示;法人有权选择合同对其是否成立,但不应对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不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但应对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现行法容易使法定代表人的角色从法人的意思表示机关跃升为“负责人”,突破法人治理的制衡机制,未来立法可考虑建构统一的法人意思表示制度,淡化代表和代理的差异,并建立代表人(代理人)公示登记制度。
关键词:法定代表人;表见代表;越权行为;《民法典》第61条;《民法典》第504条
一、问题的提出
法人尤其是公司法人现已成为最重要、最活跃的缔约主体,然而,在我国私法学界,法人中的哪些人有权以公司名义缔约、法定代表人越权缔结的合同效力如何,一直聚讼盈庭。如何适用原《公司法》第16条(新《公司法》第15条)规定的越权担保,更是有名的争议问题,催生了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
之所以产生这些争议,核心原因是我国现行法有关规定并不明确。在代表权方面,《民法典》第61条第3款和新《公司法》第11条第2款均规定,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股东会)对法定代表人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民法典》第504条还规定了表见代表制度。这些规定遗留了两个问题:一是没有明确法律、行政法规对代表权的限制,是否可对抗善意相对人;二是没有明确相对人恶意时越权代表合同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第2款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前述混乱,其最突出的新意在于,它区分了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越权代表的两种类型:一是超越法定限制,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所涉事项应由法人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作出决议或决定,对于这类越权代表合同,除非相对人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否则不能主张该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但法人有过错的,参照《民法典》第157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是超越意定限制,此时原则上构成表见代表,只有在法人证明相对人恶意时,才回归越权代表。[1]这显然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有关越权担保的效力规范扩张到所有合同领域。
本文的主题是分析这一创新的意义及其局限。其主要问题包括:①我国民法学界区分法人内部的意思形成与外部的意思表达,认为前者不应影响合同效力,上述司法解释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学说,其正当性何在。②颇具中国特色的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理论以及法定代表人制度,对评价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缔约行为有什么影响。③如何界定相对人应受保护的合理信赖,尤其是如何评价相对人“不知法抗辩”。④如何认定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缔结的合同对法人的效力,该缔约行为在相对人与法定代表人之间发生何种效力。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明确将代表权法定限制界定为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法人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决定法人意思的情形。可见,虽然它与未生效合同和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都不同,但均体现了国家对商业活动的控制,具有保护法人及利益相关者的功能。
依据《民法典》第502条第2款,未生效合同是指依法律、行政法规应办理批准等手续,在未办理批准等手续之前的合同。批准等手续是合同的特殊生效要件,它实质上是公法对法人权利能力的限制。
越权行为与超越经营范围(ultra vires)的合同不同,后者指法定代表人超出法人章程规定的目的事业或经营范围缔结的合同。早在1875年Ashbury Railway Carriage & Iron Co. Ltd.v. Riche[2]一案中,英美法就认定这种合同无效。但因为公司很容易通过在章程中规定非常宽泛和抽象的经营范围如“公司有权从事董事会认可的任何的所有贸易或业务”,以规避这一限制,加之这一规则过分限制了契约自由,英美法早已废除了这一规则。[3]在法人实在说的理论框架中,法人与自然人同样为民事主体,依据宪法平等原则,立法者在没有特别正当理由时,不能限制法人的权利能力。正因如此,霍维茨认为,法人实在说最重要的价值是摧毁了基于特许权理论产生的国家对公司的管制,推动了越权规则消亡。[4]我国新《公司法》第9条第1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之外,公司可自由设定经营范围。《民法典》第505条也规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这些规定明显废除了超越经营范围的合同无效的规则。但若章程规定公司不得从事某些经营的,此时可适用《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2款的规定。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适用于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因两者机理相同,为简便计,本文仅讨论法人。
二、评价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行为的约束条件
评价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行为,首先,须坚持法教义学逻辑一致的要求。这主要关涉我国现行法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的理论和实践。其次,我国现行法法定代表人的固有特征,也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刚性制度约束条件。
(一)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
1.代表与代理的显著私法差异
在私法上,代表与代理虽最终均产生行为由法人承受的法律效果,但在我国理论中,两者依然存在以下显著差异。
一是人格的同一性。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作为法人代表机关,与法人为同一人格,其作为自然人的人格消失或者被代表人吸收。可见,代表关系中仅存在法人和相对人两方主体。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与被代理人的人格彼此独立,故代理关系中存在代理人、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三方主体。
二是法律效果的承受原因。代表人的行为乃法人自身的行为,其法律效果自然由法人承担,[5]无所谓效果归属问题,这和自然人对其行为承担自己责任的原理相同。代理行为系代理人的行为,只不过基于代理机制,其法律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而已。
三是权利的渊源及范围。代表权源于法律直接规定,无须法人另行授权,且其通常是全面的、不受限制的,[6]及于法人的全部事务。代表行为不限于民事法律行为,还包括事实行为和侵权行为。代理人则通常需要获得授权,且其代理权的范围往往受到限制,代理行为也仅限于民事法律行为。[7]
2.代表学说的两个理论渊源
在自由意志被高扬时,一个主体能否代表另一个主体,在伦理学上备受质疑,至少在康德道德哲学层面如此;加之我国理论界已不断反思区分代表与代理的正当性,故有必要分析代表学说的理论渊源。从历史和理论两个方面来看,代表制度主要有两个渊源。
(1)政治哲学中的国家代表理论。在神学中,天主教会发展了基督的两个身体理论,即耶稣具有自然身体(自然人的身体)和神的身体。其后,在英国都铎时期,世俗法学家发展了“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论,以解释国家如何被代表、如何被呈现。它认为,国王有两个身体,即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前者和其他人的身体一样,受制于年龄、疾病等人类生理固有局限;政治身体则完全摆脱了自然人的身体局限,是一个不死的、永续的神秘体。[8]这一理论解决了如下问题:
一是国家如何组成。“二身理论”将国家比喻为自然人的身体,国王作为国家首脑,构成“头”,人民则组成其他器官和肢体。[9]国家被解释为一个“永远不死”的共体,国王和人民一同构成了合众体(corporation)。它是永恒的组织体,既包含政体(头和肢体一起)的永久性,也包含成员的永久性。头为身体的代表,这种观念影响了法定代表人制度。中世纪法学家常用的“尊贵者将低位者吸收入自身”规则,[10]可以解释何以法定代表人可以代表法人,还确立了法定代表人在组织体中的尊崇地位。
二是王权如何传承。1609年,科克爵士在加尔文案(Calvin’s Case)中,讨论了英国王权的传递方式。国王“依其生来固有的权利”享有英格兰王国,经由王室血脉传递,“不需要任何事后的必要仪式或行动:加冕不构成该头衔的一部分”。[11]王权转移是“灵魂”的迁移,国王死后,国家的灵魂或本质转移到其继任者身上。[12]
三是身体的分离导致国王人格分离。15—16世纪,法学家塑造了一个绝对完美的国王拟制人格,国王作为自然人,一个人即可构成一个“法人”,即“一人(独任)法人”(sole corporations)。相应地,“国王不能犯错,是英国宪法的必要和基本原则”。[13]国王即使犯错,也是其自然人犯错,而非其代表的国家犯错。
上述理论对英国法人理论产生的一个深远影响是,其认为作为独立主体的法人必须有作为其喉舌的代表人。后世有些神秘的法人有机体说赋予法人与自然人类似的生命力,与这种理念一脉相承。梅特兰在《论作为法人的王冠》一文中,虽然嘲讽了国王作为法人的观念,甚至阐释了官僚制逻辑中国王双重人格造成的灾难,[14]但是,他也激赏基尔克基于德国本土共同体精神建构的法人理论。他在其翻译的基尔克作品的前言中,这样描述德国共同体:“它不是被虚构的,也不是象征;不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也不是个人的集合名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和一个真实的人。它有自己的身体、成员和意志,自身能行动;它的意志和行为由作为其器官的人来决定,就像人通过大脑、嘴和手决定其行为一样。它不是虚构的人......它是一个群体,有群体意志。”[15]这种将法人成员比喻为法人身体的说法,显然受国王双重人格的影响。
(2)法人实在说。在私法中,代表学说直接源于法人性质学说。法人的法律构成要素通常包括成员和财产,各主体基于各种合同关系成立法人,法人不具有自然人的血肉之躯,不可能形成并对外表达其意思,只能由其成员形成意思和表达意思。为解决这一问题,实在说和拟制说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路径。
实在说赋予法人行为能力,法人可以通过其机关从事民事活动,法人的各个机关如权力机关、决策机关、执行机关等构成法人的“法律肉体”,是法人的一部分,其形成的意思均为法人意思,法人的意思通过代表机关对外表达,代表机关的行为为法人自身的行为。[16]拟制说认为,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其行为只能由法人中的自然人代理,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独立,不过基于代理的法律效力归属机制,由法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17]
我国现行法采纳了法人实在说。《民法典》第57条承认法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代理说以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为理论内核。[18]此外,《民法典》第61条第2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这种后果系法人自己承受,而非基于代理的法律效果归属机制。因此,在我国现行法上,代表与代理存在本质差异。
(二)法定代表人的中国特色
与域外大多数立法例不同,在代表问题上,《民法通则》没有将执行机关(如董事会)确立为法人的代表机关,而是借鉴了苏联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以解决法人的代表问题。苏联的法定代表人制度源于苏联时期的“一长制”。[19]这种法律移植的社会土壤是,我国当时施行计划经济,国家权力主宰经济运行,国有企业承担保障国计民生的经济重任。国家必须控制国有企业,若国有企业奉行公司章程自治,享有经营自由权,则国家难以实现对企业的全面控制,更难以通过单位体制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安排。相反,若国有企业存在“一把手”,且其由国家任命并对国家负责,企业运行采用行政机关中的科层制,国家的治理任务才能顺利落实。
法定代表人的内核是“法定”,它体现为其代表权源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民法通则》第38条将法定代表人确定为“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这多少有同义反复的意蕴:法定代表人是负责人,负责人是代表人,但结合彼时的社会环境也不难理解。《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7条第1款明确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第45条将其确定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同时要求企业应建立以厂长为首的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对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负有全面责任。”这里的“责任”无疑是对国家承担的责任。其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和公司登记实践进一步强化了法定代表人的权力:法定代表人只能由一个自然人担任,[20]而比较法的通例是,法律不限制法人代表机关人数。我国的法定代表人与前述国王的代表权类似,作为“负责人”,他/她在代表法人时,可以吸收其他法人成员的人格,从而可以一个人代表法人。方流芳教授在有关法定代表人的经典论文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在企业内部可以无所不为、居于权力核心的自然人形象,虽然在当时的政企关系中,他/她完全无法防御外部的权力干预。[21]
《民法典》第61条强调法定代表人必须为“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公司法》第10条将法定代表人的选任范围扩张到“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或者经理”,不再强调其必须为“负责人”。一方面,立法者关注了法定代表人在公司运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立法者关注了公司治理中不存在“负责人”的公司法安排。但在实践中,法定代表人因兼具董事长、执行董事或总经理的身份,往往能全面把控公司,成为事实上的实控人或者负责人。此外,在我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公章往往为法定代表人个人所控制,以便于其对外缔约。我国公众也习惯将在文书上加盖公章作为证明某个行为是公司行为的“唯一”(the)方式,而不是“一种”(a)方式,司法实践长期为这种观念背书。在这种背景下,法定代表人甚至垄断了对外缔约的权利,如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观点是,公司经理并不因其职位而享有职务代理权,只有在被授予经理权时,才能对外代理公司实施法律行为。[22]
立法、司法和社会观念均支持了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唯一代表的现实,其结果是使法定代表人僭越了其法律上“代表机关”的角色定位,进而成为公司意思的实质决定机关,最终结果是伤害甚至颠覆强调分权尤其是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
(三)组织法理论框架中的代表与代理
无论采用何种法人学说,也无论认为法人应否独立承担责任,法人都必然有其独立的意思,其作为民事主体才具有实际意义。法人的独立意识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法人如何形成其意思或如何区分法人意思与成员意思;二是若法人意思需要对外表达,应如何表达。
判定法人意思的基本依据是《公司法》等法律和法人章程,《公司法》分别规定了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以下简称“三会”)不同的职权,并授权章程在一定范围内另行规定。“三会”通过会议方式作出的多数决均为公司意思,如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董事会作出聘任经理的决议、监事会作出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的决议等。与自然人意思的形成机制相比,法人意思形成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这是因为法人意思的形成通常涉及多个自然人(股东、董事等)如何形成“共同意思”。在组织法上,法人意思只能通过严格的会议程序作出资本多数决(如股东会决议)、人头多数决(如董事会决议)或章程规定的一致决等方式形成。在满足《民法典》第134条第2款和《公司法》第27条规定的条件时,就可以认定公司形成了自己的意思。同时,为减少运行成本,公司不可能将所有事项都交由“三会”作出决议,如公司的一般、长期经营事项,基于董事会授权或商事惯例,公司董事、经理等职务代理人完全可以代理公司,且这种代理通常为多数人代理和概括代理。
一旦法人形成了自己的意思,需要对外缔约才能执行这些意思时,自然需要法人中的自然人对外表达。这种意思形成分为两类:一是需要作出单独、特别决议才能形成的意思,主要涉及对法人利益有重要影响的行为;二是无须法人机关作出决议的意思,主要为法人持续性、反复性的经营行为。无论何种情形,自然人在对外缔约时,执行的都是程序性的代表(代理)职权,若其落实的是法人的意思,则其缔约行为的效力由法人承担;相反,则适用权利外观法理。因此,一旦去除与自然人的类比和对法人生命力的想象,法人对外通过代表人与代理人表达,其效果完全相同。法定代表人和职务代理人体现的意思将不存在层次差异,超越代表权的行为与无权代理的效果也应相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1条将超越职务代理权限与越权代表的行为作了基本相同的处理,值得赞同。
三、评价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行为的价值冲突
在评价超越法定与意定代表的缔约行为的效力时,涉及相对人的信赖保护等问题,但前者存在较为特殊的价值,即基于法治原则的相对人知法推定问题。这直接影响对相对人合理信赖的认定,故有必要单独讨论。
(一)当事人的知法推定
基于法治原则,法律必须公开;法律一旦公开,就应推定其效力所及的所有主体均应知悉法律。故法谚云:“不知法并非借口”或“不知法不免责”(ignorantia legis neminem excusat),其理据如下。
其一,有助于促使公民自愿守法,从而实现法律建构社会秩序和引导人们行为的功能。霍姆斯指出,该法谚的践行将促进人们了解和遵守法律。[23]若承认不知法可以作为抗辩事由甚至免责,那么法律将完全无法发挥震慑作用,立法徒劳无功。该法谚鼓励人们不断学习并知悉法律,发现自己的法律义务,使法律秩序对重要社会行为的规范成为公民必备的知识。
其二,避免司法因不知法抗辩而遭遇无法裁判的困难。当某人以其实施受法律审查和评价的行为时并不知悉相应的法律为由进行抗辩时,若法院予以认可,则其将陷入相当繁复的事实审查工作中。而且,即使法院愿意审查,行为人在行为时是否知悉法律,也通常无法查明。
其三,引导社会行为的法律规范是合理的,至少符合社会习俗。这一法谚最初源于刑法,其基本假定是,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了解刑法。最初的刑法规范针对的是自然犯,它们无须公民专门学习就能知悉和掌握,是每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实践理性必然习得的知识。在报应论论者或伦理学家看来,刑法代表着根深蒂固的道德和社会规范,任何人违反刑法都应受到惩罚,无论其是否知道刑法。若行为人确实不知道刑法,在道德上同样应受责难,也因自己未能吸收这些社会基本规范而负有道德责任。[24]
然而,“不知法并非借口”的适用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与惩罚正当性的冲突。对于惩罚的正当性,不同法谚之间存在评价冲突。例如,“不知法并非借口”与“不知法不为罪”,在违法性认识错误方面就截然对立。从惩罚的正当性角度来看,只有在行为人知法犯法时,其承担法律责任才更能发挥法律的震慑功能;反之,在行为人不知法也承担责任时,对个人的惩罚效果和对社会的潜在震慑效果未必理想。按照法经济学的思路,一个熟稔法律的人,将在守法与违法之间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后选择行为,守法推定并不会改变其任何行为。但那些无法获得法律知识或法律咨询的行为人,则可能因不知法而承受更高的行为成本,[25]尤其是在法律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
二是行为人知法可能性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国家职能不断扩张,逐渐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领域的管制规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贯彻和实施这些管制规范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断提升这些管制法益的重要性,辅之以较重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在刑事领域,这催生了大量的行政犯或法定犯规范。此时,即使在“不知法并非借口”诞生的刑法领域,行为人知悉刑法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传统的自然犯如杀人、放火等,适用这一法谚虽然没有争议,但对法定犯而言,适用这一法谚可能产生背离民众法感情的后果,如针对捕杀某些鸟类的行为作犯罪评价等。而且刑法本身逐渐条块分割,如税法等领域均存在特殊刑法规范,[26]刑法的复杂化使行为人学习法律的成本飙升。
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在作为部门法、保障法的刑法越来越复杂时,可以想象其他部门法尤其是行政法的细密程度,此时要求民众通晓法律难免强人所难。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刑法领域对这一法谚的适用首先出现了松动,主要体现在偏离固有社会道德规范的法定犯领域,法院逐渐承认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构成有效抗辩。[27]例如,在美国,在涉及枪支的犯罪领域,这一法谚“正在消失”。[28]我国学者也认为,自然犯时代诞生的这一法谚已很难适应法定犯年代的刑事政策要求,[29]或主张因法定犯的空白罪状使公民难以知悉刑法,行为人因空白罪状不具备违法性认识的,应减轻处罚。[30]
在刑法以外的大量行政法领域,行为人因不知法而违法更是司空见惯。这些监管规范往往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非专业人士即使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也很难理解和掌握,如证券领域的监管规范。尽管适用“不知法不为罪”难免有损监管规范和执法机构的权威,但美国基本排除了非专业的临时投资者违反监管规范的法律责任。但是,当监管规范针对的是某种存在固有风险的活动时,行为者若不知法,可认定其存在过错,不能免责。此外,若承认不知法抗辩将严重损害第三人权益时,行为人应补偿第三人。[31]在私法领域,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180条规定,允诺人不知道一个不重要的法律且可被宽宥时,可以寻求救济。
在私法领域,对于如何推定行为人是否知法,我国法院以往多区分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如对有关公司担保的法律规范,法院一般认为,从事担保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应知晓,如“上海某发展银行、江阴市某金属锻造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32]但要求非法律专业人士知晓法律,则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如“陈某某、合肥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33]《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恰好改变了这种裁判规则,其出发点是对所有民事主体的知法推定。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的代表权法定限制包括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受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实际上,代表权的法定限制关涉公司等主体的重大利益,且其涉及的交易基本无关公共利益,故属于民事基本制度范畴,依据《立法法》第11条,其应由法律调整,行政法规原则上无权限制。二是限制的具体方式为法定代表人在缔约之前,法人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或执行机构必须作出决议,形成交易意思表示。
按照权威解释,《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主要调整《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的事项,[34]如第15条、第135条等。实际上,《公司法》还有大量限制代表权的规范,主要涉及公司及股东重大利益或利益冲突的事项,如公司向第三人增资、公司合并、自我交易、篡夺公司机会等。对代表权的法定限制均基于交易的特殊性质,具有正当性。这种规范构成法人意思形成的“游戏规则”,与民法规定的无行为能力人原则上不具有缔约能力的规则性质相同。正因如此,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为代表权的本质界限,应为相对人所知。[35]此外,在我国,公司的历史并不长,这些规范虽具有自然法品格,却很难说是实践中形成的自然规则,但这些规范若不推定当事人应知,则将使法律失去变革社会的力量,社会将永远维持现状,故推定当事人应知并不会造成不良影响。
(二)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在现代私法中,信赖原则和相互尊重原则、自决原则、自我约束原则等,均构成正当法的原则。[36]相对人若基于对法定代表人缔约权的信赖缔结了合同,其信赖应否受保护及保护程度,涉及信赖保护与知法推定的冲突。
通常,权利外观越明显,信赖保护就越合理。在超越法定权限的代表行为中,法人机关决议是法定代表人的授权来源,相对人对其授权来源本应与代理中的相对人的审查义务相同,[37]但在我国,因自然人的职位存在法定代表人、董事、总经理等差异,按照一般社会观念,不同职位的人形成的缔约权外观存在差异,尤其是法定代表人具有更显著的缔约权外观。《民法典》对不同职位形成的虚假缔约权外观的信赖保护确定了不同规格。对超越代表权的行为,第504条确定的规格是,除相对人恶意外,代表行为有效;对职务代理涉及职权范围的限制,第170条规定的是“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对表见代理,第172条则规定相对人“有理由相信”才能构成。在权利表征上呈现“法定代表人—职务代理—意定代理人”的强弱差异。因此,对法定代表人的信赖在我国民法上位于信赖保护金字塔的顶尖。然而,在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时,这种差序保护格局必须变革。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将《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确定的越权担保规则上升至适用于一般合同领域,即相对人应尽“合理审查”义务。这蕴含了两层意义:一是相对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对代表权的限制为由,主张适用《民法典》第504条确定的表见代表的法律效果;二是相对人应基于限制代表权的法律规范审查代表人的缔约权,若审查后未能发现法定代表人越权的,可以主张表见代表。
依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界定的越权代表类型,相对人需要审查的内容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寻找法律规范,确定法律是否明确规定了法定代表人在缔约之前,需要取得法人的哪一个具体机关作出决议,以及决议是否为特别多数决。例如,依据《公司法》第135条,相对人接受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的30%时,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而且需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二是若法律授权章程规定,则相对人应承担审查章程的义务,这又分为两种情形:①章程规定了决议机关。此时相对人应审查章程规定的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是否作出了决议。②章程未规定决议机关。对于越权担保,学界一般认为应由股东会作出决议,[38]因为公司担保关涉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加上股东会中心主义的公司治理框架。但新《公司法》强化了董事会在审查经营中的职权,且法律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此时不宜对当事人的知法义务要求过高,故应认定无论是董事会还是股东会决议均可。
相对人合理审查采用理性人的注意标准,应在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中取得平衡。[39]相对人合理审查针对的是对法人机关已经作出决议的审查,若法人没有作出决议,根本谈不上合理审查。鉴于法人决议为多数决,相对人首先要审查决议是否达到了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多数决。相对人还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核查股东的身份,在形式上确认签字或盖章的主体为公司股东。
若法律授权章程规定法人机关对特定交易作出决议,此时章程自然应获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相对人应按图索骥查阅章程。此时,章程规定的事项都可对抗合同相对人,如决议机关、决议通过的条件、对外担保金额的限制等。例如,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担保需经代表3/4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则相对人应审查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或盖章的股东的表决权是否达到3/4。《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8条规定,公司不能以担保金额超过法定限额等事由抗辩债权人;《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8条规定,若2/3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公司担保,则无须公司决议,担保也对公司发生效力。这两条规定忽视了代表权法定限制情形下相对人的章程审查义务,均不妥当。例如,某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对外每年只能提供100万元以内的担保,且需股东会80%以上的股东同意方可对外担保。若持股70%的大股东想对外提供担保,但股东会同意的股东表决权比例未达到80%,大股东依然制作了所谓的股东会决议,且向相对人提供了200万元的担保。在这种情形下,相对人在审查公司章程时未审查章程对表决事项和担保数额的特别约定,显然不构成合理审查。
适用合理审查标准最疑难的问题是,相对人有无义务审查决议是否满足了全部成立要件。在实践中,这主要针对法定代表人伪造股东或董事在决议上签字或盖章的情形。相对人虽无力审查签字或盖章的真实性,但相对人若通过股东或董事核实,完全可以确定公司是否召开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及签字或盖章的真实性。若相对人按照《公司法》第27条审查决议是否成立的全部要件,其交易成本相对高昂。但为平衡各方利益和核查成本,相对人应负担一定的核实义务,包括核实是否召开过股东会和董事会、同意决定的股东表决权比例或董事的数量是否达到了法律或章程规定的最低数量。
四、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行为的具体法律效果
依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超越代表法定权限的行为若构成表见代表,合同对法人发生效力,并无讨论必要。需要讨论的是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表见代表时各方之间的重要法律效果。
(一)相对人与法人之间的合同效力
1.合同对法人的效力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均规定,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缔结的合同对法人“不发生效力”,这并非《民法典》规定的合同效力类型,存在解释空间。这种合同的效力存在两种解释路径。
(1)合同成立,但效力存在瑕疵。这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简洁的思路。其出发点是,在事实层面,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行为为职务行为,其性质为法人行为,故其缔约的合同成立;不过在法律层面,需要对其进行效力评价。这种评价结果又分为两种。
一是合同无效。19世纪,普通法的普遍规则是,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无效,因为法人缺乏相应的权利能力。[40]然而,法人对越权代表的事项具有权利能力,不过法律对法人意思形成的内部程序作了强制性程序要求,法定代表人不能单独对外代表法人。因此,认定这种行为的效力唯一需要考虑的是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在相对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时,其信赖不值得保护,否则将使强制性法律规定形同虚设,甚至鼓励相对人和法定代表人恶意串通。
我国司法实践主流观点认为,相对人恶意时,担保合同无效。[41]在解释论上无效的路径包括两种:一是按照反面解释,并基于法律不保护恶意者的法理,将其解释为无效。[42]二是认定相对人应当知道其缔结的合同需法人内部形成决议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在法定代表人未取得决议时与其签约,可类推侵权责任法上的自甘冒险,不应获得法律的特别保护。[43]
二是合同效力待定。《民法典》为区分代表与代理,未整体上规定无权代表的法律效果。大陆法系国家因不存在类似于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其董事对外越权代表公司的行为,往往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44]我国学界也多以代表与代理在构成、功能、机制等方面基本相同为由,主张在《民法典》未提供充足的越权代表规范时,可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范,即将越权行为缔结的合同评价为效力待定合同,[45]效力取决于法律规定的法人机关是否作出追认决议。
上述效力认定的理论预设是,法定代表人作为法人的代表机关,其角色与代理人迥异,法人通过法定代表人从事或实施的行为,与自然人的行为并没有差异,无论其代表权的范围如何,其行为都是法人的行为,越权行为也是法人行为。而且,《民法典》第504条规定的是“越权代表”而非“无权代表”,与《民法典》第61条保持了融贯性和一致性,体现了法人与法人代表机关之间的固有法秩序和同一性。[46]此外,法定代表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实施的侵权行为即使是故意侵权行为,法人也将承受其法律后果,基于举重以明轻的解释原理,越权行为也应由法人承担法律效果。
(2)合同不成立。本文主张,代表权超出法定限制时的缔约行为,应认定为合同对法人不成立,即法人和相对人之间并不成立合同关系。理由如下:
第一,《民法典》第504条是第61条和第62条的例外规定。《民法典》第61条和第62条是关于法人所有行为法律效力归属的一般规定,第504条则为越权代表的特别规定,后者体现了法律尊重法人内部规定和法律强制规定的意思形成机制,认可了法定代表人对外表示的意思并不一定是法人的意思。
第二,代表权法定限制规范为私法上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代表权法定限制规范的实质是确定了法人从事特定交易时的特殊意思形成机制,只有经由法律规定的法人机关就法定事项作出决议,才能认定法人形成了缔约意思。这剥夺了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形成意思的权利。这些规范实际上将法人的意思形成分为两种:①法人依章程、内部授权规定或商业惯例自由形成意思,法定代表人的意思往往为法人的意思;②法人必须依据私法强行法形成意思,法定代表人的意思不构成法人的意思,其未经法定决议机关作出决议的代表行为,构成法人的意思与对外表示的意思不一致。
这里以新《公司法》第15条(原《公司法》第16条)有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的决议程序规定为例。以往,我国法院一般将其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如“某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某某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47]等。这一认定明显混淆了公法与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新《公司法》第15条是私法强制性规范,它是对公司对外担保程序的法定要求,其规范的重点是公司内部法律关系,[48]它与代理人应获得授权才能与相对人缔约的要求完全相同。而且,鉴于公司担保对公司及其股东利益影响巨大,公司章程不仅不能排除新《公司法》第15条的适用,也不能通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将公司对外担保事项概括性授权于法定代表人。
第三,类推适用新《公司法》第27条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规范。新《公司法》第27条新增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规范,其原理是公司决议必须通过召开会议并作出多数决的方式才能形成,借此区分公司行为与公司中的自然人(控股股东、董事长等)行为。如控股股东在没有召开股东会时,在名为公司股东会“决议”的文件上签字,即使其所持股权已满足多数决的比例,也不能认定该“决议”为股东会决议并代表公司意思。同理,代表权的法定限制是公开的,按知法推定原则,相对人应知道就特定交易缔约,法定代表人的单独意思并非法人意思,故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不成立。
第四,《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在越权代表情形下,法人有过错的,参照《民法典》第157条承担赔偿责任,并没有规定直接适用,而《民法典》第157条规定的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无效等情形时的法律效力。可见,它并没有将法人作为合同的主体,合同对法人“不发生效力”意味着合同不成立。
2.法人能否追认合同
《民法典》第504条并没有规定在越权代表场合,相对人恶意时,法人可否追认合同效力。比较法一般认为,法定代表人越权时,可类推适用无权代理法理,合同被法人追认后可对法人发生效力。[49]我国学者也认为,法人有权追认。[50]我国在司法实践中也予以承认,如在“深圳市某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诉某电器(深圳)有限公司、无锡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51]中,法院认为,公司未经决议程序为股东清偿债务,相对人未对公司决议程序进行合理审查,该清偿行为对公司不发生效力,但公司有权选择是否追认。
无论是超越法定还是法人内部对代表权的限制,法人均应享有追认权,理由是:①相对人有与法人缔约的意思表示,并有追求合同生效的意思,基于契约自由原理,合同对其发生效力,符合其缔约时的意思。在法人决议补正代表权瑕疵后,相对人若拒绝缔约,显然有违契约自由。②在越权代表缔结的合同中的相对人愿意缔结合同,但法人并非合同相对人,故该合同可认定为构成要约,法人可在依法作出决议后承诺。或者,认为这种合同虽然成立,但可类比《民法典》第502条规定的“未生效”合同,将其界定为私法上的“未生效”合同或需要经过批准才能生效的合同,[52]法人在依法作出决议后,合同发生效力。
(二)法人对相对人的缔约过失责任
私法对当事人因某些法律错误而从事的法律行为会给予一定的救济,以权衡“知法推定”的合理性及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53]例如,美国《合同法重述(第二次)》第153条规定,当事人不知道某项会对其缔约决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法律规定,可以解除合同。在Reich & Binstock, LLP v. Scates案中,法院裁定,即使合同因违法不可执行,不知道法律的当事人也可获得补偿。[54]
在我国法定代表人制度框架中,法定代表人的过错被作为法人过错,故在担保合同不成立[55]或无效时,法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或侵权责任。《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0条规定,若相对人明知法定代表人超越担保权限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7条改变了这一立场,转而规定在公司担保场合,若相对人非善意,且法人对担保有过错的,应参照其第17条有关担保无效的规定,即承担“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其依据是,我国采法人实在说,法定代表人为法人机关而非代理人,其过错为公司过错。[56]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会认定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的缔约行为存在过错。大多数法院认为,公司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存在过错;二是对公司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监管存在过错。例如,“陈某明、黄某幸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57]认定,公司在“法定代表人的选任及行为约束、印章管理等方面,亦存在过错”,故应承担赔偿责任。一些法院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故存在过错,如“李某嵩与周某、海南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58]一些法院甚至直接因为公司没有作出决议,就认定公司存在过错,显然是将法定代表人的过错等同于公司过错,如“李某、赵某某等股权转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59]和“文某与张某、逯某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60]等。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要求“依法依规认定上市公司对违规担保合同不承担担保责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9条落实了这一要求,但仅适用于上市公司。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顶格判决公司承担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的赔偿责任,这很容易架空《公司法》规范公司对外担保的立法目的,损害公司利益。公司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唯一路径,只能是依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3条,证明法定代表人与对方恶意串通,然而在实践中,公司又将遭遇举证难的障碍。
在相对人非善意时的公司担保情形下,为缓解越权代表时公司对外担保承担的过重赔偿责任,较多学者基于越权代表人与无权代理人法律地位高度相似等理由,主张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和第4款有关无权代理人的责任,它们都没有涉及被代理人的合同责任或赔偿责任,故类推适用的结果是,对相对人非善意情形的越权担保,公司既不承担担保责任,也不承担赔偿责任。[61]反对者则严格区分代表行为和代理行为,认为类推适用无权代理缺乏依据。[62]
实际上,在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下,若相对人非善意,即使不适用类推,也能得出法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解释结论:其一,相对人应当知道法人没有形成缔约的意思,如前所述,这种缔约行为系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行为,与法人无关。其二,在代理场合,代理人与被代理人通过代理权发生法律关系,而按照一般社会经验,某人授权他人代理并不常见,相对人通常有较重的审查义务,故在不构成表见代理时,被代理人无须对相对人承担责任,以使民事主体免于被他人强行“代理”还需担责的恐惧。在代表场合,虽然当事人将法定代表人等同于法人符合我国普遍观念,但在法律已明确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并非法人行为时,就交易行为而言,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距离并不比代理人与被代理人更近。故按照类推原理,被代理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时,“被代表”的法人也不应承担。然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已明确规定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57条,故在司法实践中,唯一避免法人赔偿责任扩大化的方式只能是确认法人没有过错,至少过错程度较低。
(三)相对人对法定代表人的权利
1.相对人能否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
在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的缔约情形下,若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我国学者或不区分相对人恶意的具体情形,一概肯定相对人可请求法定代表人履行合同或承担违约责任,[63]或认为相对人只有在因过失而不知越权代表时才享有这一权利,且可以选择向法定代表人主张履行合同或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向法人主张缔约过失或者侵权责任。[64]本文认为,在相对人恶意时的超越法定代表权缔约情形下,相对人不享有这些权利,理由如下。
第一,无法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与第172条的功能相似,均旨在保护善意相对人的信赖,不过两者保护的信赖程度有所差异,故法律效果也不同。前者适用的前提是相对人为善意,即不知代理人无权代理,且不知不存在重大过失。[65]在越权代表缔约情形下,相对人为非善意时,不具备本条规定的核心构成要件,故无从类推适用。
第二,《民法典》第171条第3款有其特殊的立法政策。该款保护的是当事人的积极信赖利益,但事实上,从信赖保护原理无法推导出其规定的法律效果。[66]依据契约自由原则,相对人在缔约时已明知其系与被代理人而非代理人缔约,若合同在相对人与代理人之间生效,不仅违反了代理人的意思,也违反了相对人的意思。该款规定的正当性基础只能是信赖保护,对相对人非善意时的越权代表缔约,该款自然无类推适用的余地。
2.相对人能否请求法定代表人承担赔偿责任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并没有规定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责任。法定代表人应否对相对人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两种观点:肯定说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67]否定说的理由主要是严格区分代表与代理。[68]
在实践中,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权限,通常都存在明显过错,此时无须类推即可证成法定代表人对相对人的赔偿责任,其理论路径包括两种:一是基于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了缔约中的第三人责任,但与德国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判然有别。此时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57条,认定法定代表人和合同当事人一样,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二是基于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规定的无权代理人责任,其性质为侵权责任,原因在于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合同法上的特别结合关系,而仅为社会生活中的一般交往关系。[69]因我国侵权责任保护的法益非常宽泛,相对人也可对法定代表人主张侵权责任。
五、结语
对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行为的效力评价,根本上是合同法与公司法的关系问题。传统民法将法人缔约意思作为其内部事务,[70]认为其真实意思的有无或瑕疵均不影响合同效力,合同法仅关注其外部的意思表示是否存在瑕疵。《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传统认知,值得肯定。
法律限制法定代表人权限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法人及其成员和相关利益主体不因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对外缔约而遭受损失。就这些特定交易事项,一方面,法律承认法人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另一方面,法律对法人内部如何形成意思进行程序控制。在我国,这些限制性规范主要见于公司法,其目的正当、内容合理、程序正义,已经具有自然法品格。若认定相对人不知晓法律规定构成善意,将永远无法实现法律建构正当商业秩序的目的,故《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20条第1款强化这些规范的拘束力具有正当性。
认定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权限订立的合同效力,最为核心的问题是该缔约行为是法人的行为,还是法定代表人作为自然人的行为。这很容易将其与法人的性质勾连在一起。法人性质是法人学说史中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基尔克甚至将法人性质之争上升到“古罗马vs.日耳曼”的民族主义高度。在《德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立法者虽然刻意回避了法人的性质之争,但事实上依然以有机体说(organtheorie)为基础设计法人制度和规则。[71]在英美,梅特兰引介基尔克的法人理论后,“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20年左右达到高潮,学者对公司人格问题的研究近乎痴迷”。[72]然而,无论何种法人学说,都很难解释今天的法人制度和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它们都并用了拟制说和实在说。[73]就本文讨论的超越代表权法定限制问题而言,法律限制的路径是区分法人的意思形成与意思表达。就这些事项,法定代表人对外表达之前,必须由法律规定的其他法人机关形成法人意思,故法定代表人超越法定权限的行为不构成法人的行为,而应归于自然人的行为。
若不拘泥于某种法人学说,法人制度中的代表和代理的区分将不再重要。我国的法定代表人制度在法人治理实践中已滋生诸多积弊,被学界诟病多年。未来可以考虑两个方向的改革:一是构建统一的法人对外意思表示制度,统合法人中的法定代表人和职务代理人;二是为减少实践中大量的表见代表和表见代理纠纷,法人的代表人和代理人应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在信息社会,这无疑是避免虚假权利外观成本最小的方式。
注释: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248页。
[2](1875)L. R.7 H. L.653.
[3]Stephen J. Leacock,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Ultra Vires Doctrine in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Commonwealth Caribbean Corporate Common Law: A Triumph of Experience Over Logic, 5 DePaul Bus.& Comm. L. J.67(2006).
[4]Morton J.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88 W. Va. L. Rev.221(1985).
[5]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六版),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页;施启扬:《民法总则》(修订第8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6]BeckOK BGB/Schöpflin, 70. Ed.1.5.2024,BGB §26 Rn.12.
[7]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8]Richard Hyland, On Rereading the King’s Two Bodies: Robert E. Lerner, 66 Am. J. Comp. L.458(2018).
[9]参见[德]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6页。
[10]参见[德]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0页。
[11]7 Coke Report 2 a77 ER p378.
[12]Richard Hyland, On Rereading the King’s Two Bodies: Robert E. Lerner, 66 Am. J. Comp. L.458(2018).
[13]Guy I Seidman, The Origins of Accountability: Everything I Know about the Sovereign’s Immunity, I Learned from King HenryIII, 49 St. Louis L. J.393(2005).
[14]Frederic Maitland, The Crown as Corporation, 17 Law Quarterly Review 131-146(1901).
[15]Otto Gierke,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trans.,1927),1990,(translator’s introduction),xxvi.
[16]参见[日]山本敬三:《民法讲义Ⅰ·总则》,解亘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17]参见王利明:《民法总则研究》(第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18]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19]参见刘道远:《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角色、制度渊源及其完善》,载《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
[20]参见李培根:《法定代表人法律地位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
[21]参见方流芳:《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3—4期。
[22]参见迟颖:《职务代理权的类型化研究——〈民法典〉第170条解释论》,载《法商研究》2023年第1期;反对意见,参见钱玉林:《经理地位的法律逻辑分析》,载《法学》2010年第8期。
[23]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Boston, 1881,p.48.
[24]Henry M Hart Jr, The Aims of the Criminal Law, 23 Law & Contemp. Probs.401(1958).
[25]Stewart E Sterk, Accommodating Legal Ignorance, 42 Cardozo L. Rev.213(2020).
[26]Michael Cottone, Rethinking Presumed Knowledge of the Law in the Regulatory Age, 82 Tenn. L. Rev.137(2014).
[27]Dan M Kahan, Ignorance of the Law is An Excuse - But Only for the Virtuous, 96 Mich. L. Rev.149(1997).
[28]Mark D Yochum, The Death of A Maxim: Ignorance of Law is No Excuse(Killed by Money, Guns And A Little Sex),13 St. John’s J. L. Comm.635(1999).
[29]参见王俊:《违法性认识理论的中国立场——以故意说与责任说之争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22年第5期。
[30]参见张旭、陈凯琳:《无违法性认识减轻处罚之证成》,载《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3期。
[31]Stewart E Sterk, Accommodating Legal Ignorance, 42 Cardozo L. Rev.213(2020).
[32]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2023)苏0281民初19933号民事判决书。
[3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皖01民终10658号民事判决书。
[3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245页。
[35]参见陈自强:《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36]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37]参见潘运华:《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载《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7期。
[38]参见高圣平:《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39]参见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以〈合同编解释〉第20条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24年第1期。
[40]最典型的案例为Ashbury Carriage Co.v. Riche, L. R.7 H. L.653(1875).
[4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319页。
[42]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555—557页。
[43]参见迟颖:《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效力与责任承担——〈民法典〉第61条第2、3款解释论》,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4期。
[44]参见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日]我妻荣:《新订民法总则》,于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45]参见朱广新:《法定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
[46]参见邹海林:《公司代表越权担保的制度逻辑解析——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5期。
[47]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裁定书。
[48]参见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9]参见[日]近江幸治:《民法讲义I:民法总则》(第6版补订),渠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3页。
[50]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24年版,第555—557页。
[51]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苏02民终983号民事判决书。
[52]参见蒋大兴:《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3期。
[53]参见李俊青:《“法律不知有害”质疑》,载《北方法学》2016年第3期。
[54]455 S. W.3d 178(Tex. App.2014).
[55]《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时,其效力可参照适用《民法典》第157条有关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和确定不生效的规定。
[5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8页。
[57]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0802民初6332号民事判决书。
[58]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23)赣0502民初8360号民事判决书。
[59]浙江省宁海县人民法院(2023)浙0226民初5679号民事判决书。
[60]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2023)豫0811民初5415号民事判决书。
[61]参见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6期;王建文:《〈民法典〉框架下公司代表越权担保裁判规则的解释论》,载《法学论坛》2022年第5期。
[62]张家勇:《论越权担保无效时公司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载《法学》2024年第3期。
[63]参见刘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5期。
[64]参见潘运华:《越权代表行为效力规范释论》,载《政治与法律》2024年第7期。
[65]参见冉克平:《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释论》,载《现代法学》2020年第2期。
[66]参见杨代雄:《〈民法典〉无权代理人责任制度的解释论》,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67]参见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载《现代法学》2021年第6期。
[6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1年版,第137—138页。
[69]参见纪海龙:《无权代理人过错责任及其减免——〈民法典〉第171条第4款解释论》,载《法学》2023年第1期。
[70]参见蒋大兴:《论公司外部表示行为的法律逻辑》,载《现代法学》2024年第3期。
[71]BeckOK BGB/Schöpflin, 70. Ed.1.5.2024,BGB §26 Rn.12.
[72]Morton J Horwitz, Santa Clara Revisi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Theory, 88 W. Va. L. Rev.217(1985).
[73]参见谢鸿飞:《论民法典法人性质的定位——法律历史社会学与法教义学分析》,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6期。
作者:谢鸿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法学杂志》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