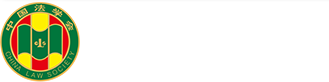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 孟红艳
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于2019年12月1日实施,其第九十八条规定,只有功能上无法达到治疗效果的药品才能被认为是假药。2020年12月颁布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删除了刑法原第一百四十一条中“本条所称假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这一条款,本罪的处罚范围由此大幅度缩小。根据药品管理法对“假药”范围的重新界定,对擅自销售有治疗功能的仿制药或其他药品的行为,目前实务中都不再以销售假药罪定罪。但是,实务中关于“药品”认定的其他难题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近年来,在处理生产销售假药刑事案件中,对于生产过程中的药材替换行为,例如,某公司在生产护肝片时,原本应该使用药材南北柴胡,却使用了有一定功效但存在明显价格差异的四川竹叶柴胡替换的,司法机关直接根据药品行政监管部门的鉴定意见,认定行为人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参见杨隽、黄勇:《替换原料生产中成药行为的定性》)。这种在行政违法和刑事责任之间画等号、根据行政违法认定判断犯罪的思考方式是否妥当,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必须看到涉药品刑事案件的认定在当前仍然有很多难题,尤其在如何理解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保护法益、“假药”范围等方面,依然存在未竟的话题。而上述争议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理解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的行刑衔接问题。
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应当立足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应当认为,刑法上的判断虽然要顾及前置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必须从属于前置法,更不意味着前置法上的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之间仅存在量的差异。前置法与刑法的规范目的存在重大差异,前置法的相关规定对于犯罪认定最多只能提供有限的指引。违反前置法只是有构成犯罪的高度嫌疑,但被告人是否真的构成犯罪,必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结合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和规范目的、刑法的谦抑性等进行判断。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应当以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为核心进行独立判断。换言之,刑事违法性在“质”上就应当有别于前置法的违法性。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能完全从属于行政法。前置法的违法性只能为刑事违法性的判断提供线索或者有限支撑,刑法上考虑前置法的取向不等于从属于前置法,为了防止轻易地将行政或者民事违法认定为犯罪,限定处罚范围,必须重视刑法所固有的违法性判断。强调刑法违法性需要独立判断时,是为了对行政违法上升为行政犯罪的范围进行一定限缩,即违反行政法的,未必构成犯罪,以彰显刑法的谦抑性,从而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只是部分地入罪,而不会将所有违反行政法的行为都作为犯罪处罚。
由此可见,并非违反药品管理法的行为都构成刑事犯罪,刑事不法判断具有相对性。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之下,肯定违法性具体判断的相对性,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行刑衔接问题。
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应当坚持实质判断的方法论
有观点认为,生产、销售假药罪侵害的法益是国家的药品管理秩序。但是,这种观点过于形式化。在现代法治社会,所谓的行政管理秩序不具有终极的法价值或目的,秩序的最终价值或目的根本上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将行为是否侵害了公众的生命健康作为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保护法益,才是更为妥当的结论。生产、销售假药罪不是仅仅为了保护某些抽象的药品行政管理秩序,而是意欲保护特定的、与构成要件紧密关联的法益。换言之,国家建立药品管理秩序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在行为没有对公众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及其危险性时,不宜将涉及药品生产、销售的行为认定为生产、销售假药罪,刑事违法性的判断并不绝对从属于药品管理法,对“假药”认定,刑法上应当相对独立地进行判断,在行政违法的基础上考虑刑法谦抑性进一步予以限缩。
认定生产、销售假药罪应当顾及法益侵害原理
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规定,因此,本罪在性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但其成立与否也需要具体判断行为是否会危害人体健康。根据这种法益观,对于刑法上“假药”的认定就不是形式上的。为此,应当建立从刑法视角实质地判断“假药”及涉药品犯罪的类型化标准。例如,对于实务中发案率较高的在中成药生产过程中的平价药材替代、药品成分轻微改变等行为(如前述以四川竹叶柴胡替代南北柴胡生产护肝片),替换或改变后药品不符合国家药典对该种药品处方药材的规定,但其主要成份基本相同,临床效果没有显著差异的,可以认定其违反药品管理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但对其不宜按照生产、销售假药罪论处,以此实现刑法谦抑性。
(本文系最高人民检察院2024年度检察应用理论研究课题《涉药品刑事案件办理实务问题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