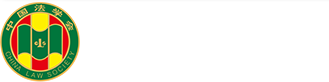文/李军 宋元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在依法侦查徇私枉法等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时,同步追究关联行贿人刑事责任的需求日益凸显。然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对行贿犯罪管辖权的分割配置,导致此类案件办理面临严重的“监检管辖冲突”,表现为程序衔接梗阻、侦查效率低下、风险防控失序,严重削弱了对系统性司法腐败的打击效能。本文从法律体系协调性、侦查权配置科学性、程序效率价值及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权完整性等维度,系统论证徇私枉法关联行贿案件由检察机关并案管辖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提出针对性的立法完善方案及可行的实践操作路径,旨在破解管辖困境,提升腐败犯罪治理的系统性、精准性与实效性。
一、徇私枉法关联行贿案件管辖的现实困境
在通过对某省检察机关五年来办理的徇私枉法类案件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案件存在行贿情节且达到立案标准的共有145件,通报监察委的共有137件,把行贿犯罪当成共犯处理的有13 件。
(一)效率损耗与时机贻误。
当检察机关在侦查徇私枉法过程中发现关联行贿人,因无行贿罪管辖权,需依据《监察法》有关规定启动跨部门通报程序。此过程涉及线索评估、层级审批、文书流转等环节,耗时普遍较长。在跨地域指定管辖案件中,异地监委介入需重新履行立案程序,沟通协调难度倍增。宝贵的侦查窗口期在等待中流逝,极易导致嫌疑人潜逃、串供、毁灭证据或翻供。
(二)司法异化与功能减损。
为规避前述程序风险与效率损耗,实践中出现将关联行贿人勉强认定为徇私枉法罪共犯处理的趋势。此做法虽在个案层面解困,却严重违背刑法基本原理和长期司法惯例:行贿人通常缺乏共同实施徇私枉法行为的故意与行为,不符合共犯构成要件,强行入罪有违罪刑法定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破坏了“单纯行贿请托不按共犯处理”的司法共识,造成同种行贿行为因本罪管辖机关不同而定性与处罚迥异的司法割裂。此现象是现行管辖制度运行不畅导致的次生危害,不仅扭曲了法律适用,更削弱了反腐败的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暴露了改革的紧迫性。
现行管辖分割是造成徇私枉法关联行贿案件查处效率低下、风险剧增、司法扭曲的结构性根源。在检察机关管辖的特定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关联行贿犯罪的管辖权配置亟待系统性改革。
二、管辖冲突的立法根源与程序梗阻
困境的深层原因在于现行立法体系的内在冲突与实践程序衔接的失灵。
(一)法律规范冲突:管辖权的制度性割裂
核心冲突在于:《监察法》第11条: 赋予监察委员会对包括行贿罪在内的贪污贿赂类职务犯罪的全面管辖权。《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保留检察机关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虐待被监管人以及徇私枉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14个特定罪名的侦查权。
当行贿行为是实施上述特定司法渎职犯罪的手段或动因时,同一犯罪事实链条被人为割裂:司法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由检察院侦查,而行贿人的行贿行为却由监委管辖。这种割裂直接违背“关联案件并案处理”的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无视犯罪事实的内在统一性。无论相关受贿行为最终是作为“徇私”情节、择一重罪处罚还是数罪并罚,检察机关在侦查本罪时,对关联的行贿人天然缺乏管辖权,导致侦查权能残缺。
(二)程序衔接梗阻:跨部门协作的实践难题
现行监检衔接机制(《监察法》第3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操作层面存在问题:一是流程繁琐耗时。线索移送需经历内部评估、审批、文书制作与流转、监委受理评估、决定立案(或不予立案)反馈等环节,链条长、节点多。二是信息壁垒与协调成本。部门间沟通机制不顺畅,信息共享不足。在跨地域案件中,协调层级更高、难度更大。三是风险点集中。嫌疑人失控,移送等待期是嫌疑人脱控、实施反侦查行为的“黄金时间”。证据固化困难,时过境迁可能导致关键证据灭失或证人记忆模糊。侦查中断,检察机关在等待期间难以围绕行贿线索开展深入侦查。认识分歧与重复劳动,对线索价值、证据要求理解不一;监委介入后可能需重复询问、核实,增加泄密风险。
(三) 被迫扭曲:规避风险的司法异化
如前所述,将关联行贿勉强按共犯处理,是制度缺陷倒逼的司法异化,其危害性深远,进一步印证了改革的必要性。
立法导致的管辖权割裂,叠加程序衔接的失灵,在实体上割裂了牵连关系,在程序上制造了梗阻与风险,在实践中迫使司法扭曲,形成系统性障碍,严重阻碍对徇私枉法及其关联行贿犯罪的合力打击。
三、检察机关并案管辖的正当性基础与比较法镜鉴
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徇私枉法等特定司法渎职犯罪关联行贿行为的并案侦查权。其正当性植根于以下方面:
(一) 实体法基础:牵连关系的本质要求
行贿行为(手段)与徇私枉法等渎职行为(目的)常构成刑法理论中的“手段-目的”型牵连犯。基于犯罪事实内在的紧密联系,由同一侦查机关负责侦查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效率优势。《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8条关于“对于一人犯数罪、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等情形,可以并案侦查”的规定,其精神内核契合处理牵连关系的管辖原则。犯罪事实的统一性不应被管辖分工人为割裂。
(二) 检察侦查权的历史沿革与内在逻辑
检察机关曾长期统一管辖包括贿赂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在现行保留其对特定司法渎职犯罪侦查权的框架下,将紧密关联的行贿犯罪纳入其中,是保障检察侦查权完整、有效运行的逻辑延伸和内在要求。避免因管辖分割导致的侦查权“跛脚”现象,确保对损害司法公正行为的查处形成闭环。
(三) 宪法与组织法依据:法律监督权的应然范围
宪法第134条确立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是其职权的根本来源。《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20条具体授权其“对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进行侦查”。行贿行为直接腐蚀司法公正的根基,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源头和有机组成部分。若检察机关只能侦查司法工作人员渎职的“结果”,而不能触及促成该结果的关联行贿“原因”,则其法律监督权在侦查环节是残缺的、不彻底的。并案管辖是保障法律监督权完整性、实效性,实现对“损害司法公正”行为进行源头性、系统性监督与惩治的必然要求。
(四) 比较法镜鉴:域外管辖制度的共性启示
域外法治发达国家在处理关联职务犯罪管辖问题上,呈现出显著共性:一是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并案侦查权。《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3a条明确规定:"检察官对于与职务犯罪存在事实关联的贿赂行为,可以行使延伸侦查权。若受贿行为与滥用职权行为具有目的实现上的关联性,应当合并侦查。该条款通过"事实关联性"标准,赋予检察官对牵连贿赂犯罪的当然管辖权。二是日本检察厅法中的侦查优先权。《日本检察厅法》第6条规定:"检察官认为有必要追究与职务犯罪相关联的行贿行为时,可以自行开展侦查,不受其他机关管辖限制。该制度确立检察官在牵连案件中的侦查优先地位。三是俄罗斯、法国等。普遍实行由一个强力机关集中侦查存在紧密关联的贿赂与渎职犯罪。
域外立法例呈现三大共性特征:牵连关系作为管辖联结点,普遍承认犯罪事实的内在关联是合并管辖的基础。侦查权集中行使原则,由一个主管机关负责关联案件的侦查,避免分割带来的效率损失和风险。程序措施即时衔接机制,在并案框架下,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可无缝适用于所有关联方,极大提升效率、降低风险。
域外经验有力证明,由同一侦查机关对关联行贿与渎职犯罪实施并案管辖,是符合侦查规律、提升犯罪治理效能的有效制度,为我国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四、立法重构的具体方案与实践路径设计
(一) 核心立法建议
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二款后增设但书规定:“对于与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虐待被监管人以及徇私枉法、民事、行政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枉法仲裁、私放在押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犯罪存在紧密事实关联的行贿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并案侦查。”
(二) 配套制度与实施细则
一是明确启动与审批程序。检察机关在侦查上述本罪过程中,发现存在紧密事实关联的行贿犯罪线索,经检察长(或分管副检察长)批准,即可启动并案侦查程序,无需再移送监委。二是规范线索处理边界。对于在并案侦查中发现的非关联的行贿线索、其他职务犯罪线索或涉案的其他公职人员线索,仍应依法移送监察机关。三是优化监检协作机制。建立安全、规范的涉密信息共享平台或机制。完善并案决定、重要进展及处理结果的事后通报机制,必要时进行事中沟通。明确对关联性认定、线索移送范围等争议的解决途径。四是强化检察机关侦查能力建设。针对新增的贿赂犯罪侦查任务,加强侦查人员的专业培训(审讯策略、证据审查、金融调查等),更新技术装备,完善侦查指挥体系,确保“接得住、办得好”。
(三) 实践推进路径
一是试点先行与经验积累。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选取若干省份或针对徇私枉法关联行贿等典型案件类型,开展检察并案管辖试点。通过试点检验方案可行性,积累操作经验,发现并解决实际问题,为全面立法修改提供坚实的实践支撑和优化建议。二是司法解释与政策指引。在立法修改前或试点期间,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司法解释或工作指导意见。明确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对与检察机关管辖的特定司法渎职犯罪存在“紧密事实关联”的行贿犯罪,可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8条进行侦查的理解、适用尺度和操作规范,为基层探索提供合法合规依据。三是强化内部协作与专业培训。检察机关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与刑事检察、法律政策研究等部门加强沟通协作,统一对关联性认定标准、证据把握、法律适用等问题的认识。开展针对性的全员培训,提升检察人员办理此类复杂交织型贿赂-渎职犯罪的能力和水平。
结语
赋予检察机关对徇私枉法关联行贿犯罪的并案侦查权,绝非部门权力之争,而是基于犯罪事实内在联系、遵循诉讼经济规律、提升腐败治理效能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创新。它是破解当前管辖困境的“钥匙”,是优化国家监察权与检察权配置关系、落实宪法第127条“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互相配合”原则的创造性实践。通过打通程序梗阻、降低执法风险、遏制司法异化,此改革将有力提升对司法领域系统性腐败的源头治理和精准打击能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和法治权威。我们期待并呼吁立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采纳这一方案,也恳请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和推动这一符合司法规律和反腐败斗争需要的变革,为构建更加科学、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职务犯罪侦查体系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李军,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宋元,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